电影理论:自在、自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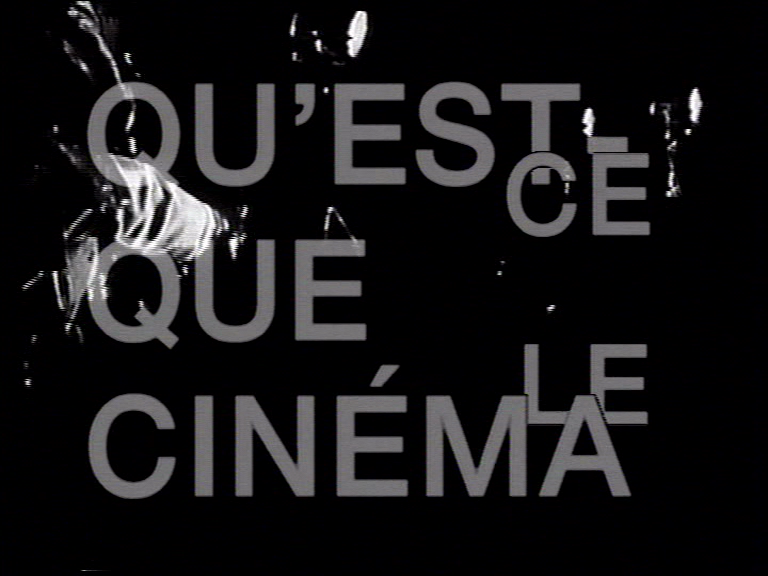
Qu'est que le ciné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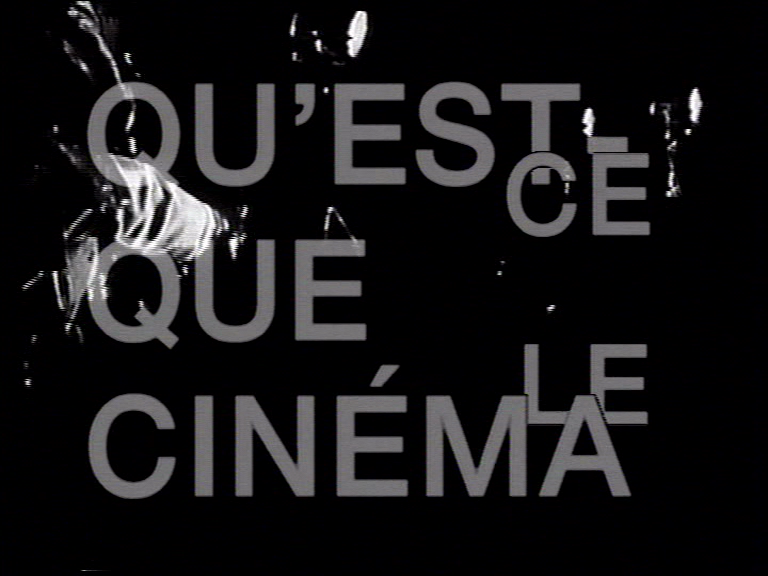
作为「个别问题与讨论」课程的学期作业,探讨我深思颇久的「理论实践」问题,该是蛮恰当的时机。然而浸淫在电影理论的学习算不上长也称不上短的时间里,某些意向性的问题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对我来说,所有的电影理论都有其可取、可供学习之处。毕竟这些都是方法,都是研究电影的利器,它们不见得都得在什么时间出现,但却经常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看起来,我对电影理论们的宽容似乎不让我对它们产生什么疑惑才对,但面对有学问的各个大家的说法来讲,那些分歧又教我感到困惑,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他们?
于是在探讨的过程中,思索这些问题时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可能代表不同时期自己的某些自问自答。或许我已经过了那个迷惑的阶段,重新看待这些理论时,我已经能够截长补短,为各个理论修修补补地,看能否建立比较健全的分析方法。但问题是,理论本身是无辜的,但理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教我头痛。
如果理论、对象(大多是指电影)之外还加入了对象的对象(当然,也就是指电影观众),那么这三角关系是不是牵扯出更为复杂的连带关系。然后我们看到电影理论家们,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降的理论,掺杂着各式各样的人文理论或概念,注入电影分析中以复杂但却具有更多想象空间的论述与工具。似乎看电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它跟我。而是它与它中的它(他、她、牠)与我之间的问题。
然后,我在主题尚处于模糊未定的情况下,开始了以下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列有纲要,却没有精确的内容,我想,既然是问题,也要讨论,那么某种「过程性」是需要被记载下来的…
当崔君衍老师与阎啸平老师不约而同地谈到作为电影理(评)论的里程,巴赞(André Bazin)似乎还是这个领域的最终回归,那么是不是在他逝世五十周年的今年,再回头看巴赞,他的价值何在?
对我而言,巴赞的著作一直可以被我称为「旧约圣经」,倒不是说它严峻到得以与旧约相比,而是它所建立下来的基础与某些不变本质则是我永远的参考指标。尤其当目前我们可见的一些电影文论,不论是出现在《当代电影》或者是《电影艺术》等学术期刊的,乃至于台湾的《电影欣赏》,那些动辄上万字的文字,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这点同时也由崔老师提出与我讨论过。而巴赞又何以能在两、三千字的篇幅中将如此鞭僻入里的观点,镶嵌在那些引人入胜的文字流动里。我们或许能说,那个思考电影的时代已经不再,或多或少我们能说那是在一场风气之中,就说「新现实主义电影」好了,当电影评论形成某种风潮时,这些思维彼此的激荡下,产生了巴赞。一如我们从《电影是什么?》(Qu’est-ce que le cinéma?)书中,巴赞对意大利评论家(同时也是理论研究者)阿里斯泰戈(Guido Aristarco)的回应(见〈为罗西里尼一辩〉一文)就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理(评)论家的相互作用。我们当然更不用提同样来自法国的艾弗尔(Amédée Ayfre)、阿杰尔(Henri Agel)、米特里(Jean Mitry)、莫兰(Edgar Morin)、甚至新浪潮《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派的诸将等;即便是在德国遥相观望的克拉考尔(Siegried Kracauer)与爱因汉姆(Rudolf Arnheim)也一样。这那样的「思索电影」的风气之下,也在电影评论界里掀起了一波「浪潮」。而今天,我们自然能够在一些理论史(评)书中对这个发展过程有个清晰的概念,举凡阿里斯泰戈的《电影理论史》、阿杰尔的《电影美学概述》(Esthétique du cinéma)、安德鲁(Dudley Andrew)的《主要电影理论》(Major film theory)以及布朗(Nick Browne)的《电影理论史评》、奥蒙(Jacques Aumont)等着的《当代电影分析》(L’analyse des films)等。只是说,当我拿这些理论相互参照,并希望拿来对影片作分析时,自然而然会遇到某些操作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是什么?
好比说我于「视听语言」的期末报告中分析了小津安二郎的《小早川家之秋》(小早川家の秋)的一段戏。然后我透过相对精确的方式去将那个场段中的每个镜头走位以及其空间配置与时间性作为结合,然后导出小津电影中的空间魔术,可能来自于某种「日常困惑」的表现。但这对我来说至少有一种危险性,即我是以「小津电影表达了日常」这个假设作为前提,在唯物的分析太度与方法上进行分析而将种种证据推向这个大前提。然而,我却以为我的分析中,几乎不包括任何我学过的理论与分法。
此话讲得有点太极端。首先,要问两个问题,其一是所谓的「日常困惑」是指什么?第二,难道对于小津电影中这份表意性不能看做其作品的现象学倾向吗?先不论「日常困惑」的概念为何,但假设小津电影着重「将观众纳入电影中」这样的基本强调下看来,这份现象学走向则相当明显。
芝诺!残忍的芝诺!伊利亚芝诺!
你用一枚箭穿透了我的心窝,
尽管它抖动了,飞了,而又并不飞!
弦响使我生,箭到就使我丧命!
太阳啊!……灵魂承受了多重的龟影,
阿基利德不动,尽管用足了飞毛腿!
——梵乐希(Paul Valery)《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
[译文引自阎啸平老师〈回到狄德罗〉。]
我犹记在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篇名字就叫做〈日常困惑〉的小说中惊讶于文中将一种日常惯性错觉以夸张化表现为一种近乎超现实的体现(当然,我们因而将他摆在文学史上从表现主义过度到超现实主义,然后牵连到现实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中,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份出自于对「日常」的过度习惯产生的错觉与偏差,同样可以拿来描述我们人对于日常习惯性的某种衍生行为,好比才刚锁完门就马上忘记自己是否锁过门。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小津将人物置于一个人物所习惯的空间中,然后,让人物对于这个习惯空间做出他所该有的反应:即忽略某种理性计算,而纯粹任由身体对时空做出自然反应。但对我所分析的段落来说,我首先并没有挑选出跟观众有关的桥段,即使我们观众对于这样的一场戏绝对能够感同身受,或至少说我们能理解片中这个场段的意义以及所有牵涉到的人物的行为举止。但我更相信这个场段牵涉到的更多是来自于导演所要传达的「感知」性。这份感知被赋予在空间的设定以及人物的表现上。
但,要知道,光是对于「时间」或者「空间」的处理,这个分析同样可以从诸如柏区(Noël Burch)的《电影实践理论》(Praxis du cinéma)或者鲍德威尔(David Bordwell)的《电影叙事》(Narration in Fiction Film)等书籍中找到蛛丝马迹。然而为何你不相信是自己在这些理论的熏陶中,不知不觉内化到体内了?
或许我不能否定此点,但我想表达的是说,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分析报告,对于观者又有什么样的帮助?而巴赞那些人那样地建立美学系统的方式,我如今只能靠着这种微小的分析报告,指出,或者证明某些已然存在的假设,比如刚刚说到关于小津的假设或既有的说法。就好比我刚刚说我已经有一个假设,那个假设还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读来的,然后我的分析只是在补强这个假设罢了。
难道你想要就这样独创一个什么美学出来吗?在这么多理论的森林前再种上几株小树苗,难道能够有任何的成效?再说,难道你自己又认定读过所有的理论了吗?然而如果你只是指出一个关于作者论的分析报告练习,就抱怨理论成形的困难,会不会是小题大作与偏离主题了?
或许是说,我不甘心自己的创见最后只依附在别人的说法中。虽然知道说自己的补强其实多少也是丰富了某种既定说法,这在将来肯定会成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但现阶段来说很难看出它们的潜力。而且当初1960年代西方对于「作者论」的笔战,也确实经常让人对于这类别的研究感到不安,看不见前景…
但要知道,目前针对作者为主要聚焦研究的还是相当的多,再说,只要电影不断发展,就还会有新的史论产生,而电影史一如所有其它历史一样,都跟人有关,也就是说,都有被默认的作者,而这个被默认的作者,不是别人,就是导演。再说,不管什么历史,也就是人的历史。
这点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也试图透过「人」的比较,当那些比较文学的盛行老爱拿跨媒体来讨论艺术的异同性,或许,或许真的有相当创新的发现,一如台湾学者刘纪蕙曾针对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芳名卡门》(Prénom: Carmen)里头使用的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弦乐四重奏使用有什么样的新意时,确实写出了一篇深入人心的研究。然而这当然也是因为电影作为集合艺术,任何优秀的电影作品都至少能找出一两项这类跨媒材的表现处理。然而我倒觉得回归到电影本质上的探讨似乎更为吸引我。
比如说?人物的比较不就很像是某种电影史研究?
我想,从前阎啸平老师教导我看电影,就是要我从两个方向出发,一是对于异种艺术表现形式的关切;第二就是要先熟悉电影史。不过我之前要做的事情还要多一些。比如,虽然也是阎老师的提议,建议我研究「饮食电影」,然而那份研究没有持续进展是好的,毕竟并非我们挑选研究的电影都那么值得细心探究,好比我们挑的其中一部是李安的《饮食男女》,这影片独立存在着似乎也不是什么拙劣的作品,但摆在其它一同探讨的片单里头,像是小津的《秋刀鱼之味》(秋刀鱼の味)、布努埃尔(Luis Buñuel)的《资产阶级拘谨的魅力》(Le Charme Discret de la Bourgeoisie)、艾索(Gabriel Axel)的《芭比的盛宴》(Babettes gæstebud)等电影之前,显然就变得渺小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对于饮食这件事一窍不通的我,实在难以接下这项研究。尤其当我想到我还得因为研究这个主题而需要反复看格林那威(Peter Greenaway)的《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 Her Lover)这样的电影时,那才是真正的煎熬。
换言之,你自己的喜好是如此严重地左右你的研究方向吗?
不瞒你说,这是真的。尤其当我在研究时得不断地面对某些文本时,假如没有强烈的喜爱,研究的过程就会变成相当艰苦的事情。后来,我擅自改动了研究方向。我再次回头找我最爱的小津安二郎,然后决定将他晚期最后六部彩色电影根据它们的特质,对应起六部欧美电影。希冀从这样的对照中,看出什么研究的乐趣。
这份研究达到了你电影理论实践的实质效果了吗?
坦白说,没有。首先,这个研究并没有完成。即便我把这个研究当作准备到北京考试的一种考前准备,因而以每个月一次的方式,找了同好朋友一起陪着我这样进行分析研究,看影片并且讨论,但我最终却没有写出文章,甚至最后两次的比较连研究的纲要都没有拟出来。
但,你的这份研究确实有什么样的新意吗?
我认为是有的,只消看看我把小津分别对应上刘别谦(Ernst Lubitsch)、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奥菲尔斯(Max Ophüls)、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柏格曼(Ingmar Bergman)与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大家绝对会将他们看成迥异的几队人马,但殊不知其实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相通性的。套一句阎老师说过的话,要套方法来谈东西一定都可以谈,只是看怎么谈罢了。
你觉得这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作者关系树枝图吗?
远远不是那样的,我倒觉得自己是藉此练习学过的那些电影分析方法,比如谈小津与刘别谦这个组合,就谈一下剧本结构的问题,其中还牵涉到表演这个项目,当然连带要将好莱坞体系做一个简单的对照;谈到希区柯克,则从观点与空间这两项出发…诸如此类的。但我感觉是会遇到瓶颈的,比如说当谈到费里尼时,免不了要拿精神分析来引述一番,同时还得借用后现代思潮的一些概念,虽然当代的电影理论其实与这些当代思潮脱不了关系,好比法国的《电影手册》不也三番两次与哲学、文学界巨擘举行访谈,比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Roland Barthes)等。虽然这些人本身也经常在著作中谈论电影,所以其实跟电影界没有太大的隔阂。这些人里头最有名气的也就是德勒兹(Gilles Deleuze),这位曾经发表过两部巨大电影专书的哲学家在他的电影著作发表之后,我们似乎有一个新的电影理论视野,但或者又可以看成某个终结。即便它们由于种种原因,遭到反对者的讪笑,然而它们或许也不能称为「电影理论」。对于德勒兹的争论我想暂时还没有一个盖棺论定的结论,即使他已经铿锵有力地坠地(跳楼自尽)。但他两本书基本上甚至成为我的「新约圣经」。它们的份量要与巴赞一样,永远值得我去探究其文字的含意。
那么这样看起来,你所欣赏的电影理论(我们姑且称这些都是理论)与其说贴近影片本身,不如说更要求思维过程。
对的,这点我也曾与崔老师轻轻碰触到。当我称赞奥蒙那本《蒙太奇爱森斯坦》(Montage Eisenstein)的书多么有意思时,他却更多推崇德勒兹这类「思想式」的电影论述。可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个危机性。其实梅兹(Christopher Metz)派对德勒兹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其中最难推翻的也就是「精确度」的问题。符号学自己认定作为一门「类科学」的学科时,似乎是走向文本的精确研究与分析。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像巴赞那样谈电影又脱离影片多远。不过假如德勒兹对电影的研究真如传言那样,许多影片的案例来自他两位影评朋友当内(Serge Daney)与波尼泽(Pascal Bonitzer)的转述,那么德勒兹会那么说「一套电影理论不“涉及”电影,而是涉及电影所引发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本身同其它实践的相应概念具有某种关联。一般来说,概念的实践没有理由优于其它实践,而概念的客体也没有理由优于它种实践的客体。事物、存在、影像、概念等所有事件类型都是在多种实践相互牵涉的层次上形成的。电影理论不针对电影,而是针对电影的概念,同电影本身一样,是实际的、有效的或实存的。伟大的电影作者与伟大的画家或伟大的音乐家是一样的:对自己的创作谈的最好的就是他们自己。但是,他们在谈论时却变了样,变成了哲学家或理论家,甚至连弃绝理论的霍克斯(Haword Hawks)和假装轻信理论的戈达尔也不例外。电影概念不是为电影而设的,然而,它们就是电影的概念,而不是关于电影的理论。就像时间有正午和午夜之分,我们不应再问“电影是什么”,而是应该问“哲学是什么”。电影本身是影像和记号的新实践,哲学应该把它变成概念实践的理论。因为,任何技术、应用和反省的确定性都不足以构建电影本身的概念。」(注:我得参照大陆、台湾以及英文版翻译才得以完成这段引用…这显见光是德勒兹的公案本身就已经需要不停地被诠释与研究,更不用说他提出的那些概念又要再次去检视。),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所以根据德勒兹的这项声明,侯帕斯(Marie-Claire Ropas-Wuilleumier)等人对德勒兹提出的质问其实也不再重要了。这种争论好比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以「政治实用性」就全盘否定掉维尔托夫(Dziga Vertov)一样。
那么你这样的引用你称为「新约圣经」的结论,不就已经可以当作你学理论的一个终结性解答?
非也。假设我们简单将电影理论分为两类:「哲思类的」,包括本体论、现象学、哲学等领域的努力,比如巴赞、艾菲尔、莫兰、德勒兹等为这一类;「科学类」,包括精神分析、语言学、符号学、记号学等,如梅兹、奥蒙、贝路(Raymond Bellour)、柏区等(或许还要加上爱森斯坦)属于此类。那么其实中间还有一类折衷派的米特里与克拉考尔。但不管是哪类,我的游移却没能让我得到安心的状态。当我们看到柏区因为错记某些他提出来的影片案例,却因而得出颇为独创的实践方法,或者像德勒兹也从影片的错谈中导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似乎提醒我们「电影真的在于启发」。可是一旦自行操演理论实践时,不管是叙事、场面调度甚至作者论,又感觉贴近影片给研究者带来的踏实感又是其它所无法取代的。
所以…「电影理论不可能“像”它的主题对象」?
跳出这个论点似乎已经跟我前述论述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了。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好了。2006年9月在台湾由阎老师与齐隆壬合力号召的一场「欧洲电影论坛【电影符号学】研讨会」我有幸与会了。该场论坛主要以法国电影理论现况为主要讨论主题。出席的学者说是老中青三代,不过主要研究的电影理论感觉却像是老与中两个世代而已。所以主题先是有梅兹(由齐隆壬谈)与米特里(由崔君衍老师谈);然后有电影镜像叙事的文本分析(吴佩慈);再来就是1980年代以降的德勒兹(黄建宏)、侯帕斯(刘永皓),或许杜布瓦(Philippe Dubois)(孙松荣)算得上是比较新的理论家;其中还以阎啸平老师拿诗经《关雎》对「赋比兴」做蒙太奇游戏感觉更像将最为古老的理论做全新的升级。梅兹、米特里也就不用多提了,这些已然成为经典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歧见。德勒兹的情况刚刚也稍微描述过了。镜像叙事很多来自梅兹那篇谈《八又二分之一》(8 1/2)的文章;侯帕斯的「再书写」论点也好,杜布瓦的「形体」研究,都导回那些经典式的见解,前者回头从空间下手,谈布莱松(Robert Bresson)、侯夏(Glauber Rocha)以及戴维斯(Terrence Davies)或者鲁兹(Raoul Ruiz)与瓦尔达(Agnés Varda)作品;后者则从马盖(Chris Marker)、爱普斯坦(Jean Epstein)、罗伊格(Nicolas Roeg)以及朗(Fritz Lang)影片中的枝微末节去谈形体的现形。然而,问题是其中牵涉到的形体变形还包括某种储存随机因素造成的撕裂,如胶片的斑驳或发霉造成的印迹进行探讨。假如说像是柏格曼《假面》(Persona)片头那种刻意而为的变形还有得讨论,如果只是因为储存疏失而造成的断裂,像是某个德莱叶(Carl Dreyer)的《贞德受难记》(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出现一两个黑画面而被给予多余的诠释的话,这类的研究又如何真正看到影片本身。虽然孙松荣声称这才是真正「回到电影本身」,但身在结构主义时代的崔老师也很尖锐地指出这样的研究方式不就退到「电影后面」看电影。但这些有什么新?巴尔特的业余电影观,如他的「电影的第三层」意义不也是类似这样的研究方向。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才是电影理论的出路,实在仍难有个结论。当我看到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电影寓言》(La Fable cinématographique)似是新的东西,里头却也老是一些经典电影的诠释,同样透过很微小的东西出发(即便书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观点),另一方面,莫兰早在1957年的《电影,或想象的人》(Le cinema ou l’homme imaginaire)中提到电影作为「寓言」的概念…
所以照你这样说起来,似乎,已经没有「新的」电影理论了。且看来你本来看似针对现象学作为讨论的主要方向,最后也转向了。
德勒兹那句「我们不该再问“电影是什么”」像是要从巴赞出发,然后完全走出去。并且他也为自己最后的著作(《何谓哲学》)下了伏笔。只是他既没有终结电影理论,后继者似乎也表现出疲态了。然而,这样的讨论,永远,未完成…
补记:
经过这三年多的「洗礼」,我感觉应该写一篇後续来补充了。可是总是没有时间…
(编辑:AA)
View Comments
留着日后看
“第二,难道对于小津电影中这份表意性不能看做其作品的现象学倾向吗?先不论「日常困惑」的概念为何,但假设小津电影着重「将观众纳入电影中」这样的基本强调下看来,这份现象学走向则相当明显。”,此话怎讲啊?感觉有点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