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贾法·帕纳西的从影生涯,兼谈伊朗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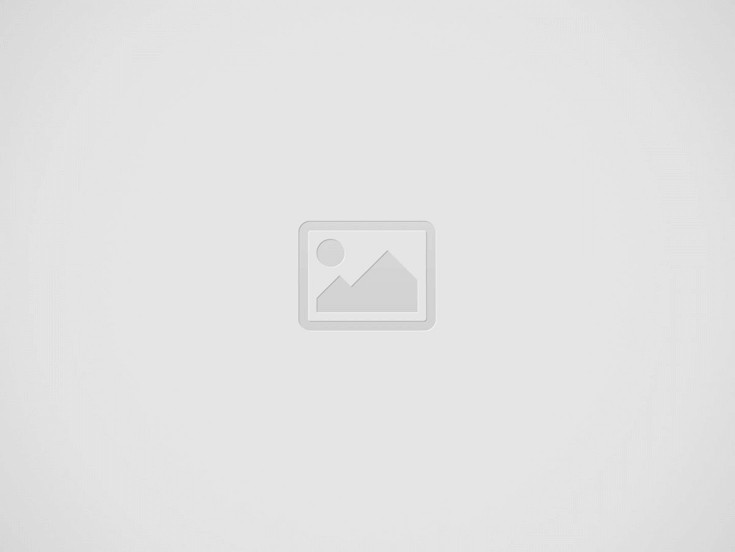

(FILES) -- A file photo taken on August 30, 2010 shows Iranian film director Jafar Panahi posing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AFP in Tehran. Jafar Panahi and rights lawyer Nasrin Sotoudeh of Iran have w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Sakharov rights prize, lawmakers said in a series of tweeted messages on October 26, 2012. AFP PHOTO / ATTA KENARE
1995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第48届戛纳电影节的闭幕式上,全世界开始关注起一位导演。那晚的金摄影机奖,颁给了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34岁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以褒奖他执导的《白气球 》(Le Ballon blanc,1995)。
那一刻,两个故事交相辉映,彼此衬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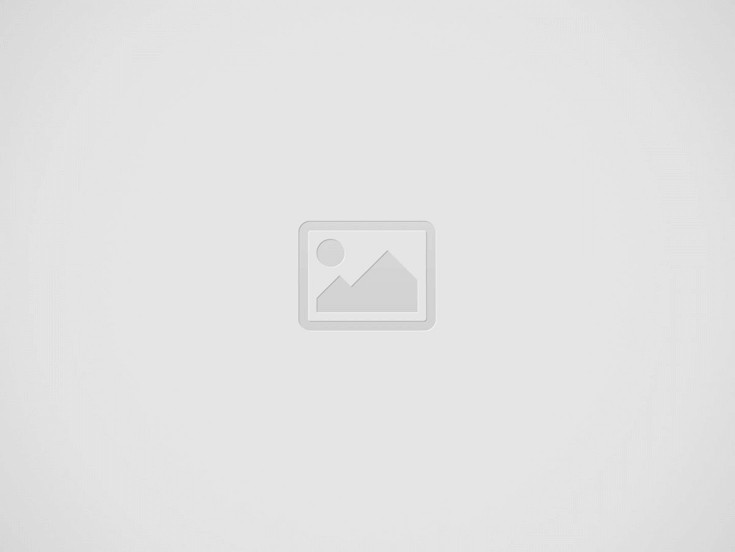

第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出生在德黑兰贫民区的男孩的个人成长史。
他是粉刷工的儿子,生长在一个几乎没有文化氛围的传统家庭。而在这个喜爱电影的国度里,经常出没于电影院已然是他与众人的常态。年轻的帕纳西,很早就对艺术表现出独特的品味和显著的才能。他20岁的时候,爆发了伊拉克对伊朗战争。在战场上,他既是士兵,又是摄影师和导演。
20世纪70年代时,他和很多同胞一样,都拿着这种便携式的摄像机——超8(super 8),尝试着当时正流行又富有创意的电影实践。退伍之后,他就读于德黑兰电影与电视学院(l’École supérieure de cinéma et d’audiovisuel de Téhéran),该学院挂靠在国家电视台下。
为了养家,帕纳西一边上学,一边还在电视台工作。他那时已经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他学生时期对于知识和实践的渴求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刮目相看,不仅自己拍了很多短片,也尽可能地参与制作其他同学的作品。无论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人们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导师基亚罗斯塔米
1993年迎来了一次决定性意义的见面——帕纳西结识了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后者还邀请帕纳西为其工作。正如他之后谈到的那样,他完全出乎意料地等到了这次机会。
基亚罗斯塔米当时已是伊朗电影界的核心人物,尽管他的国外影响力还没那么大。这次会面是指引帕纳西走向光明征程的开端,而这段征程只有通过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才能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50年代,电影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艺术,却完全被当地的电影类型——波斯电影(Le film Farsi)垄断,混合着喜剧和各种夸张的效果,歌曲和舞蹈,放荡感和大男子主义,激烈的争吵和趋俗的感伤主义。
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影响下,伊朗的年轻导演们开始拍摄更加关注现实、同时电影语言也更为大胆的影片。法罗克·戈法瑞(Farrokh Ghaffary)、卡穆兰·舍得尔(Kamran Shirdel)、艾布拉希姆·格勒斯坦 (Ebrahim Golestan)、芙茹弗·法洛克扎德 (Forugh Farrokhzad)以及苏赫拉布·沙希德·萨利斯(Sohrab Shahid Saless)被称作是伊朗新电影(cinéma Motefavet)的领头人,该运动尤以达瑞许·迈赫尔朱伊 (Dariush Mehrjui)执导的《奶牛》(Gaav,1969)为标杆。在当时巴列维独裁统治下,其中很多电影都无法通过审查。
同是1969年,政府在教育、文化部门的框架下,专门为青年人成立了一个电影组织——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电影部(le Kanoun, Institu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enfants et des jeunes adultes)。这个组织的重担落到了导演艾博尔翰·法罗热什(Ebrahim Foruzesh)和年轻的美工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身上。
作为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刚刚拍摄了处女短片《面包与小巷》(Nan va Koutcheh,1970),接着又拍摄了一些短片;作为负责人,他试图把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发展成伊朗电影独具创造力的地方。无论是拍摄“儿童电影”,或是选用儿童作为影片主角,基亚罗斯塔米都因此躲过一些审查上的障碍;而当时大多数的伊朗大导演,例如阿米尔·纳得瑞 (Amir Naderi)、巴赫拉姆·贝赛 (Bahram Bayzai)或是达瑞许·迈赫尔朱伊等等,都在大胆地自由创作,其作品通常很复杂、带有批评性,且并没有在商业领域内发行。
这种多产的氛围,即使在大革命期间也没有中断。1979年2月,巴列维王朝覆灭,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成了唯一一个从旧王朝存活下来的,它继续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培养未来的电影新星,如阿伯法周·贾利里 (Abolfazl Jalili)。
此外,该组织拍摄的“儿童电影”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严苛的伊斯兰政府审查。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Où est la maison de mon ami ?,1987)是一部儿童电影,或者说是由儿童担任主要角色的普适性的电影,它标志了伊朗作者电影在西方世界受到的高度认可。
这部影片首先在1988年的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亮相,随后是1989年的洛迦诺电影节,于1990年在法国发行,随后的几年在欧洲其他国家陆续发行。
伊朗电影的世界发展
到了80年代末,伊朗电影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突然成为了最热门之一。基亚罗斯塔米无愧是其中的领头人,也有一些其他已经被提名的导演(例如纳得瑞、贝赛和贾利里)莫森·玛克玛尔巴夫 (Mohsen Makhmalbaf)、之后他的女儿萨米拉•马克马巴夫(Samira Makhmalbaf)都发挥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他们的电影经常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露面并斩获奖项,同时在西方国家也能顺利找到发行方。而这种关注度的上升源于基亚罗斯塔米在戛纳电影节的历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续集——《生生长流》(la vie continue,1991)是基亚罗斯塔米第一部受邀至戛纳电影节(1992年)的影片,并获得平行单元“一种关注”大奖。两年后,他凭借“村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橄榄树下的情人》(Au travers des oliviers,1994),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贾法·帕纳西得以成为基亚罗斯塔米的助手,后者也因而变成了前者的导师,还为其写了《白气球 》的剧本。
这是一部典型的“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风格的影片,即使并未由该组织制作。影片在现实主义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孩子面对物质和道德困境时,做出的决定。
基亚罗斯塔米终于在1997年,凭借《樱桃的味道》(Le Goût de la cerise,1997)达到了戛纳电影节的巅峰,捧回了金棕榈奖。
这个背景对于贾法·帕纳西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尤其在伊朗,这是颇为有利、同时又问题重重的背景。很多在国外获奖的影片在国内被禁,导演们甚至被告发为“国外的间谍”、“西方的走狗”等等。没有人比基亚罗斯塔米更常遭到那些最保守的媒体的抨击:在摘得戛纳金棕榈奖之后,一群狂热分子拿着棍子和棒球棒在德黑兰机场围堵他,幸而有一群他的拥趸者保护他。
伊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美好旅程同时也是充满争执的,而帕纳西即将走到那个风口浪尖。至少《白气球》是他的作品中唯一一部官方授权发行的,在国内外都取得了成功,因而也保证了帕纳西很长时间的物质支持。
尽管是帕纳西担任《谁能带我回家》(Le Miroir,1997)的导演和编剧,但这部影片仍带有很强烈的基亚罗斯塔米的印记。
此片获得了1997年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它看起来是“伊朗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协会的电影”(题材多关注在困境中的儿童,而这部影片用偏向纪录片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必须独自乘坐公交车回家的故事)和基亚罗斯塔米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的第二部杰作——《特写》(Close-up,1990,该片证实了导演不只是会拍儿童电影)这两者的结合。
这部影片在纪录片和剧情片两者的嵌套中、在真实和虚幻切换的质疑中,达到了巅峰。它回归了伊朗电影某个旧有的主题,我们可以在伊朗最早期的电影中找到踪迹,例如欧瓦纳·欧哈年(Ovanes Ohanian)执导的《电影演员哈吉阿迦》(Haji Aqā, acteur de cinéma,1932)以及一部伊朗新电影之作——卡穆兰·舍得尔 (Kamran Shirdel)执导的《雨夜》(La nuit où il a plu,1967)。
基亚罗斯塔米对此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多部电影中进行了后设电影(译者注:在电影虚构的真实中,揭露电影的虚构)的尝试。
在《谁能带我回家》中,那个叛逆的年轻小演员在拍摄时揭露,导演让她在摄像机面前表演的虚构角色,然而这也许没有基亚罗斯塔米在《特写》中记录并重现冒牌莫森·玛克玛尔巴夫来得更为真实有力。然而,至少帕纳西第一次尝试了远离电影叙事本身,也开始真正思考他作为导演的位置。
不管他愿不愿意,这些都是他曾走过的路,十年之后,他也因此能够更加深入地去探索,而他和剧情片“自然”关系的保持已变得不再可能。
《生命的圆圈》,第一部公开的反对之作
导演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似乎是当代伊朗生存条件下的舆论使得导演走上了一条探索形式的道路。《生命的圆圈》(Le Cercle,2000)是帕纳西第一部集大成之作,让他捧回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是迈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认可,却也让他在伊朗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伊朗当局及支持当局的大批群众,认定这是他同西方妥协的新证据,并且认为只有抹黑伊朗政府、国家以及国家形象的电影才会受到嘉奖。
《生命的圆圈》事实上是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命运的正面抨击,主要是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偏离传统道路的年轻女性,那些逃脱了家庭、丈夫、或是婆家控制的女性。
三位女主人公以及其他次要角色的磨难传达了她们所遭受的迫害、侮辱以及每天不得不服从的种种限制。这样的电影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前所未有的。并非没有公开被批判的电影,例如莫森·玛克玛尔巴夫执导的《意中人的婚姻》(Le Mariage des bénis,1989),指出了1989年以来政府对革命信仰的背叛和对穷苦人民尤其是老兵的弃置。
玛克玛尔巴夫曾经是个热忱的支持者,而如今他对当局的敌意越来越深,最终他逃亡了,就像阿米尔·纳得瑞在9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
纳得瑞曾是70年代伊朗新电影的重要人物,也是伊朗后革命时代(译者注:1979年至1989年霍梅尼担任最高领袖期间)作者电影的杰出代表。
除此之外,还有达瑞许·迈赫尔朱伊的三部曲《莎拉》(Sara,1993)、《帕里》(Pari,1995)、《女人花》(Leila,1996);杰出女导演洛珊·班尼蒂玛(Rakhshan Bani Etemad)也曾用批判的方式质问伊朗女性所遭遇的处境;贾利里则专注于贫困儿童的命运。
从更深入的角度来看,所有伟大的伊朗电影,始于基亚罗斯塔米,始于他对于表层的质询、对叙事的重新探索,用更深层次的批判眼光去看待社会和这教条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是重新建立在政治生活和神圣的古兰经规定的日常生活之上的,这也构成了阿亚图拉(译者注:对伊朗等国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霍梅尼创立的伊斯兰社会的哲学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命的圆圈》更是针对女性多种状况的更加明晰和论据更充分的抨击。这样的抨击,其角色设定上的大胆和尖锐不一定能在西方世界(经常在电影中被揭露相似的状况)引起注意,却在伊朗当局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禁了这部影片。
且不论影片题材的沉重性,《生命的圆圈》很好地证实了帕纳西场面调度的能力,一种剧情和影像完美共生的能力。
此外,故事在几位女主人公之间不断循环,将她们彼此之间相联结,因而表明了这些个人境地是由错综复杂的社会、司法和精神监狱的多个层面来构成的。
镜头的内部运动与场面调度,从整体上制造出对角色的同理心,以及一种既没有缺陷又多层级体系的卡夫卡式的感觉(译者注:卡夫卡式,是指处境的荒诞与情绪的真实的统一,这里指影片中七个不同年龄的女人,涵盖各个生命阶段,构成圆圈,所以没有缺陷或者说缝隙,而这七个层级互相又关联影响,造成荒诞与真实的统一)。
帕纳西第一次拍摄成年人,他敏锐地捕捉到年轻女性的紧张、能量以及恐惧,用偏向纪录片的手法拍摄了德黑兰的街头、店铺、来往的居民、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动。
解脱于前作的影响,帕纳西完成了出色的场面调度、影片受到的国际认可以及同当局的直接冲突,这些都使得《生命的圆圈》描下了重重的一笔,也预示了他的下一部作品——《深红的金子》(Sang et or,2003)的成功。
他的意图同样也是批判性的,甚而更甚:尽管当局政府依然以代表人民的姿态出现,声称是站在穷苦人民的革命性立场上,但政府仍然要求通过一项歧视女性的政策。这部影片的核心,是揭示伊朗大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有产者对穷人的歧视。
影片的剧作再一次充满活力、戏剧张力很大,一方面体现在主人公的职业——骑着摩托车的披萨速递员,另一方面是动作片的活力——有一场抢劫珠宝店的戏。
帕纳西安排了一次真正的城市游览,从最贫困的地区到处处是豪宅的富人区,那里混住着新政府的新贵们和旧贵族,那些旧贵族通常是流亡回国的,却依然在新社会保有一席之地。
影片的表达明确细腻,暗含着对不公正的无声的控诉,它出色地塑造了一个极讨人喜欢的主角,而这个角色照理说是不该如此吸引人的。这个侯赛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被卷入一场悲剧,但这个角色在拍摄中被注入了专注细腻的情感。
比起《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更为粗糙,而且关注的主题也不如女性命运那样有话题性,所以在西方并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关注和褒奖。
不过,帕纳西凭借他的下一部长片——《越位》(Hors jeu,2006)又获得了新一轮的国际关注。重新拾起颇受西方媒体欢迎的主题——禁止女性出席体育活动场合。
他用幽默和同理心描绘了一个为了观看国家足球队的比赛,而乔装成男性的年轻姑娘的命运。她被警察识破,并和其他几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可以被看作是另一个角色的群体)一起关在了体育馆的某个角落,一直到比赛结束。
比起之前的作品,这部影片更加经典和模式化,影片最终结束于众人爆发的狂喜,超越了男性和女性的划分,共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虽然它揭露了性别歧视,但最后仍归结于伊朗人民的统一,这样的影片无疑在开拍期间就大受欢迎,并且它还是在改革派总统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主持下完成的。
然而,在2005年6月,极端反动分子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上台后,《越位》又一次被批斗禁映,它在柏林电影节获得的评审团大奖使其情况更加糟糕。
沉默中的囚犯越狱了
《生命的圆圈》、《深红的金子》、《越位》使得帕纳西成为用电影批判政府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同时他本人拒绝去国外发展。在一个政治氛围越来越压抑的国家,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专业的电影制作,帕纳西不再能够拍摄新的影片。
2009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由于大规模的选举舞弊,爆发了伊朗“绿色革命”(mouvement vert,伊朗一次大型的反政府群众运动)。帕纳西试图和另一位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趁热打铁,在运动期间拍摄一部影片。2010年3月1日,帕纳西被秘密逮捕并监禁,毫无缘由地被审问了几周,不分日夜。他的家人和几位亲近的朋友也被逮捕,不久后被释放。帕纳西所有的拍摄设备被扣押,随后他于5月25日被保释。
同年12月,他被判6年监禁,长达20年内不得拍摄影片,不得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不得离开伊朗。2011年10月,上诉被驳回,判决成立。根据伊朗的通常规定,监禁判决并非立即执行,但随时生效。自此,帕纳西生活在威胁之下。他的遭遇让全世界很多电影圈内外的人都发起了支持行动,尤其是2012年欧洲议会颁发的,同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Nasrin Sotoudeh)共同获得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Prix Sakharov,译者注:是欧洲最高人权奖)。
帕纳西首先开始寻求其他方式来自我表达,他拾起了大学时期爱好的摄影,并拍摄了一系列乌云的照片,这些照片即将在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
此外,和他的朋友纪录片导演——墨塔巴·米塔玛斯博(Mojtaba Mirtahmasb)编排、创作了《这不是一部电影》(Ceci n’est pas un film,2011)。影片在帕纳西家中拍摄,创造性地嵌套了他自身的处境,将反思和想象融合在一起。
有趣且微妙的是,影片偷偷地从伊朗辗转到了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帕纳西找回了基亚罗斯塔米实验电影中的质疑和诗意的力量,从《特写》到《十段生命的共振》(10 on Ten,2004)再到《希林公主》(Shirin,2008),试图为那些知晓其被禁止言论的观众们构建一种真实的电影回应。
摒弃了带有他个人传奇色彩的经典素材,帕纳西创造了一种既理论又活泼的电影形式,正如伟大的伊朗电影经常选用的那样,又一次在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界限中不断移动,这个影片尤其突出了“我”的位置。
虚实的显露、戏剧的张力、导演的出演以及戏中戏的设置,是伊朗电影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用间接的方式、皮兰德娄式的风格(译者注: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他的戏剧采用怪诞离奇的情节或戏中戏的戏剧形式,揭示生活与形式的矛盾),将相对主义的观点和叙事过程显现出来。
作为导演来出演影片中的导演,这很罕见。然而这在伊朗电影史上并非是第一次。
早在1932年,导演欧瓦纳·欧哈年在他执导的《电影演员哈吉阿》中扮演了导演。基亚罗斯塔米再一次地走在了帕纳西前面,他不仅拍摄了令人质疑纪录片与剧情片边界的巨作——《特写》,而且还在他的剧情片中构建了双重电影语境,例如乡村三部曲中的后两部中导演身份的内在连续性(《生生长流》的导演也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导演,在地震后寻找《何处》影片中的两位小演员),基亚罗斯塔米还在《家庭作业》(Devoirs du soir,1989)、之后的《特写》以及《橄榄树下的情人》(副导演帕纳西也有入镜)亲自出镜,到了2001年的《童心一二三》(ABC Africa)更是作为主要人物出演。
除此之外,阿伯法周·贾利里在其执导的《萨马德的故事》(Une histoire vraie,1991)中出演了本人,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在他的影片《意中人的婚姻》扮演导演,甚至在他的《电影万岁》(Salaam Cinema,1995)中出演主角——他本人。
刚才提到的最后一部电影以及非常与众不同的《童心一二三》:以其对拍摄可能性的质询、在特定时刻将摄影机移交给他人,都可以看作是《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先驱者们。
毫无疑问,帕纳西以创造性、个人色彩和独特的张力把控了他作为“囚犯”的影片进程。此外,导演还加入了其他非常当代的电影表现手法,将部分元素抽离出来,更加确切地说,是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在《狗镇》(Dogville,2003)、《曼德勒》(Manderlay,2005)中展现的精神层面的影像;或是阿兰·卡瓦利埃(Alain Cavalier)在《无法留言的留声机》(Ce repondeur ne prend pas de messages,1979)中的探索,以及《相遇》(La Rencontre,1996)之后所有的电影,得益于轻便的手提摄像机,他得以研究“第一人称单数”(关于“我”)的电影。
因而,《这不是一部电影》尽管脱胎自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当时国内四处蔓延的现实状况,它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杰作。
更加确切地说,帕纳西参照布莱希特式的风格和戏剧式的剧作、沿袭之前的方向,在里海边的家中,拍摄了《闭幕》(Pardé,2013)。
这一次,和他合作的是坎布兹亚·帕托维(Kambuzia Partovi)。之后,帕纳西再一次创造性地吸收了基亚罗斯塔米的经验,拍摄了独具匠心的《出租车》(Taxi Téhéran,2015),使他赢得了2015年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
事实上,他借鉴了《樱桃的滋味》(Ta’m e guilass,1997)和《十段生命的共振》中影像素材的力量:一辆汽车、公共场合中的私人空间、运动中的稳定画框、挡风玻璃和车窗切割而成的构图、集中在司机身上的透视布景,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相遇和波折。
角色设定为帕纳西本人扮演出租车司机,并且接受作为“导演帕纳西”被乘客认出,而那些乘客并非偶然在路上遇见的路人,而是演员,尽管并非专业的演员,但都是本色出演自己的职业(盗版影碟的贩卖者、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护士等等……)
帕纳西重新梳理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他成功拍摄了“暗藏”的第三部电影(摄影机从未出过车门)。他这一次选择了德黑兰一个绝妙的地方(出租车)——既展现了那些在法庭上极力维护他的人,真真切切的存在;又展现了那些监视他,有朝一日会将其送进监狱的人,就像虚构的阴影一样。
和《这不是一部电影》一样,《出租车》透露出对影像的思考和日常生活中银幕的存在,这一存在增加了影片的厚度,使得悲剧、喜剧、传闻、幻想和抨击都找到一席之地。
帕纳西在这片不确定的地域继续追寻着他的电影,既不是完全受限,不管怎样他还在继续拍摄,但也不能自由回应。因而他的每部作品都经历了特殊条件的重塑,也因此得以构成一部作品。
贾法·帕纳西被一股来自于意愿和本能的力量推动着,加上在各种物质、经济和政治限制下被激发的艺术灵感,使得他可以继续探索、不断创作新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