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孟宏专访:用镜头探索台湾电影的无限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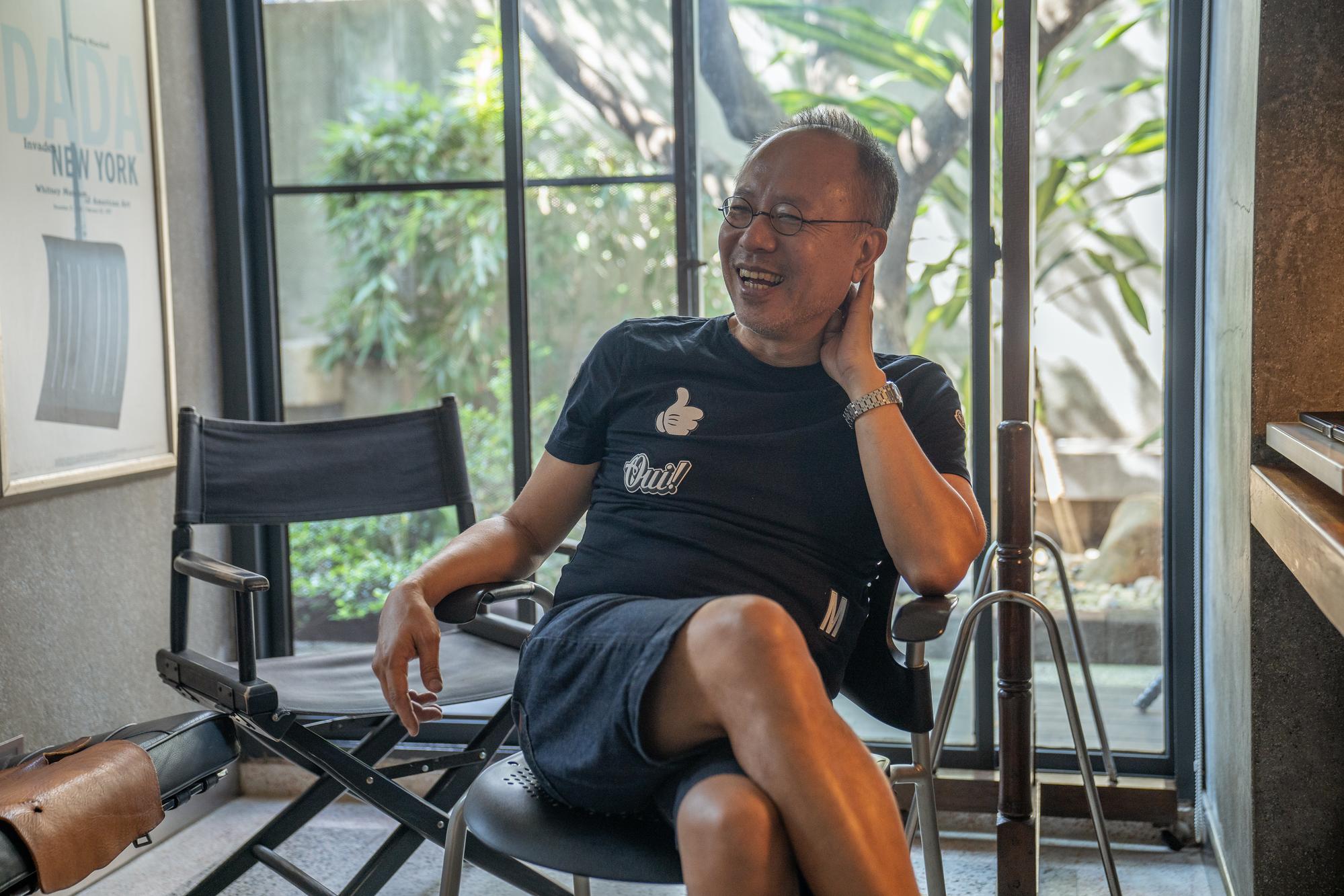
钟孟宏认为,去探索未知的创作形式,是电影最可贵的精神。 (摄影/苏威铭)
「本文转自于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www.twreporter.org)」


坐在民生东路工作室的巷子里,钟孟宏谈起台湾电影,有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决绝与深情。
「台湾新电影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失业。我1994从美国回来,台湾电影就躺平了,我没办法进入台湾电影圈工作,」他自承尊敬侯孝贤,却没有受到台湾新电影美学的影响。
▍「中国的问题,是台湾最幸福的地方」
对钟孟宏而言,电影,不只是导演个人的人文情怀,更是一国文化力量的积累与展现。
「电影绝对不是看单一导演,要看整个能量。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最幸福的地方。电影就是要有一个动能。那个动能,不是说一年可以拍一部、两部还不错的电影,那电影是要你进电影院,不自觉拍手叫好,啊,真好看!你看韩国,就是20年以后,有个东西叫做韩国电影。台湾有没有可能40年后,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台湾电影。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钟孟宏谈起台湾电影,难得有点激动。
《报导者》访谈隔天,他已跟《大佛普拉斯》电影导演黄信尧约好了,谈谈下一部片子。 「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啦,但就是要去试,」他说,一部电影的潜力,来自人的情感,而普世的情感足以跨越国际、跨越种族。
就像他第5部电影《阳光普照》,焦距落在家庭亲子,景深依然是对生命提问。
若是人生经历了点变故,青春遭遇了些打击,这样的人看钟孟宏的电影,心上难免会留下一道或深或浅的痕。
2018年的初春,屏东昌隆出生的钟孟宏,回家探望家人时,顺道绕去高雄美浓。回乡的时候,他常找好友林生祥去吃一碗越南河粉,找他的妈妈吃顿晚饭,有时,和林生祥喝酒聊天聊到半夜两、三点。这次,钟孟宏兴致勃勃讲述他的新电影计画,并且在林生祥眼前演了一场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两个年轻人穿着雨衣,骑着一辆打档摩托车,用报纸藏着两把锋利的刀去寻仇,在火锅店里找到了仇家,二话不说,拿刀砍了下去,血溅当场。
这场戏,是钟孟宏第5部电影《阳光普照》的缘起。
▍「我们太正常了,能理解得太少」
血腥的故事天天上演。但透过钟孟宏锐利的镜头,观众得以穿透眼前的现实,隐隐感到,看似黑暗残酷的人生,底层仍有生命暗涌;再狼狈的生活,也有相濡以沫的一丝金亮。
「我听到我朋友年轻时去砍掉人家的手,我吓一跳,我就花很多时间去想,他到底怎么回事?慢慢去探索,我就觉得,妈的,我们真的太正常了!我们往往用我们的理解去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能理解的大概就是眼前这一尺之方、一尺之圆而已。超过这一尺,就是陌生的、未知的,」钟孟宏说。
「世界真的好辽阔、好宽广。我有时看我女儿在桌子上,突然,笔停了,她看着某个地方的时候,我会想:她在想什么?」他自问,是否真的了解下一代?会不会,最亲密的女儿终将长成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
有一天,钟孟宏18岁的女儿去美国念书前,想看看自己父亲的纪录片《医生》。
向来不看自己电影的钟孟宏破了例,坐在女儿身边,一起看完了这部13年前惊艳台湾影坛的纪录片。女儿也像当年的观众,不解地追问:为什么片中那善体人意、聪颖活泼的12岁医生之子,会在自己的衣柜里上吊自杀?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解,我不知道,」钟孟宏坦承。
▍拒绝做「已经有答案的东西」
「做电影,或是任何一种创作形式,我觉得都是想去了解、去explore(探索)一种你不了解的东西。那是最可贵,也是最花时间的。我不想去做一个已经有答案的东西。干,我做那种东西干什么?给你一个答案?然后那个答案是我知道的?那我不是在骗你吗?」他说得直爽。
这届金马会执委会主席闻天祥曾撰文评价,钟孟宏的桀骜不驯,是台湾电影值得珍视的特质。
他每一部电影,都揭示了台湾电影新的可能。
闻天祥评论,2013的《失魂》,摆在当时一派和气、喜闹励志的电影里,是个决绝的异数,硬生生在正常与疯狂之间拉扯出一个模糊地带。 2016的《一路顺风》,那叙事的断裂,松动了类型电影的舒适感,鲜活了导演的个人标志。
「他是少数能拍出具备艺术形式的类型片的台湾导演,而且非常温柔、细腻,才能拍出像《阳光普照》这样的作品,」电影监制叶如芬说。
叶如芬也担任此片监制。她说,剧本上最后两行,一直烙在她脑海,挥之不去:
阿和骑脚踏车载着妈妈,阳光一片一片洒进落叶里,灿烂夺目。
▍一个家慢慢崩毁的过程
这部电影,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家,聚焦在一个屋檐底下的颠沛流离。
夫妻疏离,同床不同被。父子陌生,父亲老是特地跑去补习班,送笔记本去给准备考医学系的大儿子。多年下来笔记本厚厚一叠,后来才发现,大儿子一页都没写过。原来,对老是顺从父亲期望的大儿子来说,父亲口口声声「把握时间、掌握方向」,是说不出口的荒谬。
担纲演出爸爸的陈以文,形容父爱就像阳光与阴影,一体两面。
「某种程度,电影中的阿文以为这个家是靠他来维系的。但讽刺的是,也是他把家里每一个人弄到很难受的。这种两面性,就很像阳光和阴影,很难只有一个方向存在。这父亲认为自己是最苦心在支撑这个家的,但是,他所有的性格、想法和行为,却也是让这个家慢慢崩塌的,这在很多家庭里存在,」陈以文读了几遍剧本,摸索出父亲这个角色的矛盾与转折。
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像阳光,普照人间,不求回报。但《阳光普照》回头反问:如果你的爱,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呢?我还要不要?
▍爱,离了解太远,离期望太近
「所谓的父慈子孝,那些都是王八蛋,都是讲来骗人的,」钟孟宏说。
「我们常说爸妈对小孩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事实上小孩才不care你有没有条件。小孩会觉得,我才不care你的爱,我要的是了解。爱,离了解太远了。我们常听上一辈的妈妈说:我为了你费尽千辛万苦,你为什么不能了解?为什么不能体谅?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要体谅你什么?我有要你这样做吗?」他连珠炮地追问:没有了解的爱,会让子女幸福吗?
剧中陈家,是许多传统家庭的缩影。从下一代仰望上一代,充满沉重的无奈。从上一代俯瞰下一代,却又辐射出过度期望的毒素。
陈以文自己体会,剧中爸爸就是从自以为是家中支柱,不断抛出期待,后来遭逢变故,终于开始倾听家人,被动回到这个家。这个角色精采之处在于,最后为了保护这个家,爸爸竟然干了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大事。
电影中有一幕,陈以文和饰演蔡头的刘冠廷,在天台有场对手戏。爸爸拿着钱去找不断来骚扰自己小儿子的黑道蔡头,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希望蔡头不要再来找陈家人。一头橘发的蔡头散发内敛的邪气和怨气,句句笑里藏刀,拒绝了爸爸。
就是这场天台上的对手戏,埋下电影的结尾。
「别看他陈伯伯、陈伯伯喊得很亲切,但每一句话都让我难堪。这是爸爸很重要的转折,他主动要去找蔡头解决,但他发现他没有筹码,对方要的东西他是无法想像,也不知道要怎么给的。他知道这个家已经从根烂掉,这一刻,他没有别的方式,他只能用他自己会的方式,保全这个家,」陈以文解释。
要到电影最后,柯淑勤饰演的妈妈和陈以文一起爬山,穿越阳光与阴影,这一家四口那隐忍不言的伤,才让观众看见。
▍每个尾随角色的镜头,都在诉说寂寞
过去,钟孟宏的镜头下,台湾寻常的风景都成了光怪陆离的场域,暗喻剧中角色此路不通的人生即景。这次,《阳光普照》更加完美地结合了镜头语言的表演和演员表演,也让这部片入围了本届金马5个演员奖项:2位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
在《阳光普照》里,每个尾随角色的镜头,都有寂寞的诉说。
例如,爸爸孤单走在夜晚的巷子里,想着大儿子阿豪。或是,小儿子阿和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奔走在山林小径间。即使是阿豪和温贞菱饰演的女同学牵着手,走在阳光普照的动物园,都有甜美的忧伤。
人物的内心风景,和外在地理景观能卯榫扣和,是因为钟孟宏编剧、摄影(中岛长雄)、导演三位一体,让他成为台湾特别能进入角色、靠近演员的导演。
「在他镜头前表演你会很愉快、很放心。他就是坐在摄影机旁的导演,有时候就轻声说,头低一点点,这和远远坐在monitor(监看器)前导演椅上的导演是很不一样的,」陈以文说。
自称痛恨读本的钟孟宏说,拍电影就是到现场,不要花太多时间想东想西,「只要光线颜色对了,演员一站进去,氛围就会跳出来。我不会磨演员,我觉得一个演员对或错,不是他会不会演,而是导演你有没有抓到你想要的东西。」他喜欢引述法国导演特吕弗(François Roland Truffaut)的说法:没有好电影、坏电影,只有好导演、坏导演。
▍镜头、音乐,都要绝对的现场主义
钟孟宏在片场,是出了名的火爆、偏执。
饰演阿和的巫建和与饰演蔡头的刘冠廷,忘不了去年的8月1号。
台风夜,钟孟宏大叫:出班!他要巫健和、刘冠廷准备拍这部电影的第一场戏。两人顶着风雨骑着摩托车,骑了6、7个小时,转进餐厅时,突然来阵强风。这阵强风让钟孟宏很满意。但出现在电影里就是短暂的2秒镜头。
「台风天,停班停课,都还没开镜,你给我出班⋯⋯我就念制片阿忠,这样很危险⋯⋯,」叶如芬回想。
就连音乐,钟孟宏也要求「现场」。
这次创作电影配乐的林生祥,笑着说没想到,自己大萤幕的演员梦就这样梦碎了。
电影开拍后,一个傍晚,林生祥接到钟孟宏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之前讨论在告别式要使用的参考音乐不要用,这场戏3天之后要拍,叫林生祥把告别式的配乐写出来,找几个人来当告别式的乐手,直接现场演奏,拍到电影里头去。
「我觉得好疯狂,如果我的音乐没有写好,这场戏不就完了?我当晚交了一个版本。这个音乐是电影还没有开拍之前看剧本的感觉先写的,录好demo就传过去给他。隔天我再交了一个版本。第3天我马上北上,找了bass手早川彻、口琴手藤井俊充,在台北租了一个练团室,编了4个版本让他挑。隔天早上6点在台北鼎泰丰集合,前往殡仪馆拍戏,我们直接在现场就把音乐录完了。」
但电影在剪接的时候,完全剪掉殡仪馆的戏,只剩音乐。 「我原本还想当个临时演员,」林生祥开玩笑地说。
▍温暖就像吗啡,一点点就够
这也是第一次,林生祥创作出不是那么林生祥的音乐。
为了揉出这张电影配乐,林生祥不仅学习偏古典的作曲方式,自己切割不锈钢管来练习滑奏吉他,他还为一家四口每个人物都写了主题曲。给哥哥阿豪的〈动物园〉,用法国号吹出情窦初开的暖暖悸动,林生祥写了4个版本。给弟弟阿和的主题曲,旋律脱胎自《菊花夜行军》的第一首歌〈县道184〉,重新编和弦、节奏。给爸爸阿文的主题曲〈把握时间、掌握方向〉,林生祥直接跟去拍片现场,看到陈以文在驾训班沙发上夜半惊醒的眼神,有了悸动,回去很快写了用月琴、吉他、风琴3个版本的曲子。
「让音乐跟着人物,随着故事反覆出现,只要一听到音乐,可以召唤你对这部电影的感觉,那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林生祥说。
音乐里,凄怆中的一点温暖,压抑而婉约的悲伤,正符合钟孟宏绝不无聊、又绝不煽情的电影感。
「电影一感伤就像吃吗啡一样,你觉得好爽好喜欢。但是吗啡吃久了,人世间变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钟孟宏曾这样说。
就像《一路顺风》中,许多人记得的那镜头。许冠文和纳豆两个人面对面吃着小笼包,关键时刻两个小人物都没有背弃对方,为这个充满背叛与暴力的世界带来一丝微光。最后许冠文低着头快哭出来的take,钟孟宏还是剪掉了。
「一点点的温暖就够了,」他说。
▍对情感的节制,来自想摆脱过去自己
这种节制,来自成长的复杂感受,也来自想要摆脱从前的自己。
钟孟宏在昌隆农村长大,有很多老旧东西的记忆,很迷人,「但是人就要学会跟自己喜欢的东西说再见,要跟曾经拥有的书、唱片或是喜欢的电影说再见,我再也不要去看你们了。虽然,跟过去的影像说再见很痛苦,但椅子坐久了就会发烫,只要你坐上别人坐过的椅子,那种椅子上的余温还真是挺恶心的,所以就要学会跟这种熟悉说再见,努力换新的坐坐看,」他曾说。
他不太喜欢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停车》,觉得放入太多情感、和导演个人数十年的包袱。
「导演永远摆脱不了你自己的时候,不管是你过去的东西或经验,对你都非常累,对观众来讲也很累,谁要去看你那些东西?当然会觉得我有一种激情、一种抱负、一种人文的关怀或思想。但是一部电影的能量,一定不是一个导演在那边拍一个可以满足自己创作欲的小品电影而已,」他说。
那,电影到底是什么?
对钟孟宏来说,电影就是故事与人,而且人大于故事。电影应该是拍得非常扎实,平易、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邃。
他说,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分野,不过是个笑话。
「我们不是要拍赚钱、热闹、搞笑、弄IP的电影,没有,就是要拍很扎实的电影。剧本、演员、摄影、美术、音乐都弄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就是艺术了。一部电影就是这样,当所有技术能量到位以后,艺术形式就会出来。那这样的东西可不可以召唤观众?一次没有办法,再试。三次没办法,五次没办法,那不好意思,就不关我的事了,我就离开了。就这样子而已。但至少要去试,」钟孟宏很干脆。
▍即使伤口还有痕,也能走向阳光
《阳光普照》扎扎实实拍出生命匍匐前行的况味。爱与死亡的对话,如阳明山草地上的天光云影,若断时续。
作为一部台湾少见认真在悲伤的电影,《阳光普照》说透了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的一家人,狼狈靠近彼此的过程。这部电影让人感到,只要背后还有光投向前方,电影布幕就能化成绸缎,把我们擦得闪闪亮亮,擦得我们仿佛不曾在戏院暗处饮泣,擦得我们即使伤口还有痕,却能像个崭新的人,走出戏院,走向明天的太阳。
文字:王曉玟 攝影:蘇威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