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的女性电影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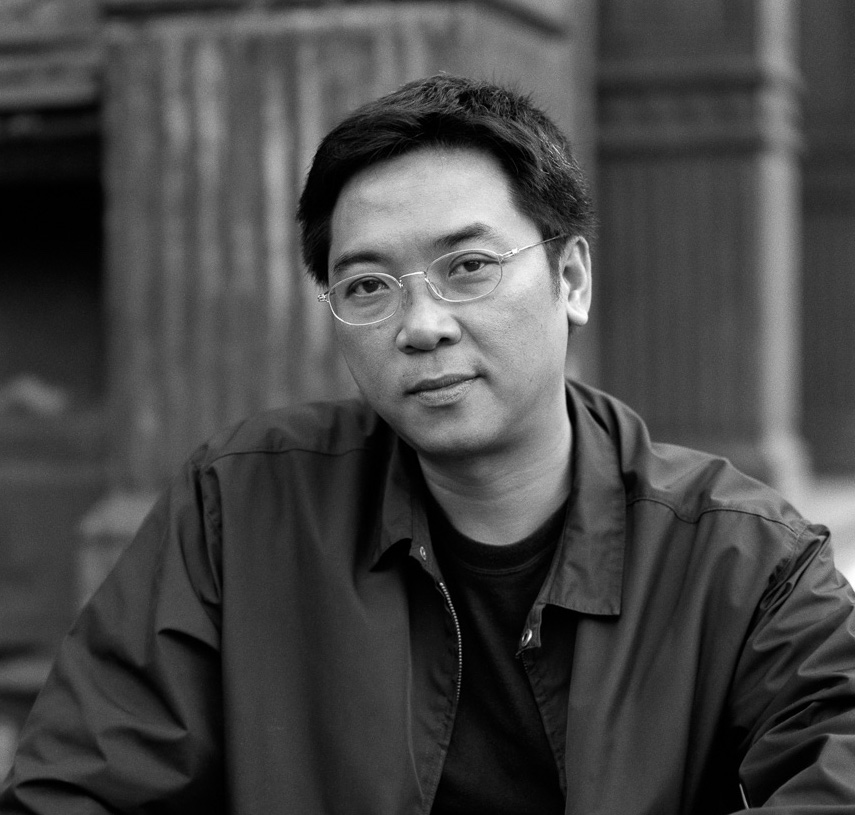
|作者:桃加
《红玫瑰白玫瑰》是少见的关锦鹏使用男性视角叙事的影片。透过无法辨认来处的、听来事不关己的旁白,倒是畅谈了几句关于“身体”与“灵魂”的辩证关系。佟振保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映照出千百年来“柳下惠”们的心中秘事,也折射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目光。
这其中渗透出些微讽刺的意味:在最后和王娇蕊的会晤中,她消失在了雨中,而振保留下了眼泪。镜头一转至第二天起床,他又改过自新,成为了好人;同样的设计也出现在《女人心》之中,孙子威年轻时拙劣的、令人羞愧的诗作其实就是邱刚健之笔,以此对自身性别进行了一番打趣似的嘲弄。
与之不同的是,同样被冠以“女性电影导演”之名的谢晋,在《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中则断然地说“拍女性电影拍得好的是男性,因为异性,他的关怀……同性有时还会有点排斥。”
然而事实却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历史被构建为男性的话语体系,在电影的语境中也同样如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观察与描绘,通常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由上至下的俯视姿态;即便不牵扯到更高层次的阶级问题,或者可以换一个更为简单且平面的词汇:一种“窥视”。
如果说倾其全力营造的苦难深重、刀山火海,究其本质是一种“想象”而无法真正具有内省式的意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关锦鹏的电影通往的是另一种路径。
在《地下情》中,“关姓女导演”作为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频频出现在对话之中,令人无法分辨虚构与否。它从某种程度上透露了关锦鹏至少于电影创作之中对自我的认知,即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故事。
《女人心》中梁宝儿和沙妞水火不容,后又坦诚相待;《人在纽约》中黄雄屏和李凤娇在餐厅互相呛声,而后居然能够雪夜对饮,给予了我们诸多浪漫的时刻——此种微妙而隐秘的感情变化,大约只有女性能够体认。同样的,关锦鹏的影片总是采用一种颇为散点式的叙事方式,“单身女人俱乐部”、三个向往明星生活的女性、三个身处他乡的女性……镜头在人物之间转动、敏感地捕捉,仿佛水流一般,其柔和的弧度在镜头的内与外十分地一致。
同样一种绵延之感也在历史、生命、地域的讨论之中:如花的鬼魂寻得十三少;阮玲玉轻轻扶住踩在椅子上换灯泡的母亲,女儿也跑来抱住她;张曼玉提及《桃花饮血记》中“真是要命”的村姑,镜头中却是她的迷人笑容;还有炒房地产的商人、舞台演员、已经嫁做人妇的纽约异客,她们在唐人街的餐馆后厨“鸭头下酒”,回溯共同的文化记忆。
但细细想来则不难发觉,在群像的勾勒中,相异的落点总是同一的。来自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即便她们的出身和生活轨迹并不相同,但最终都走向对于父亲的反抗或者冲破对于社会规训于女性所既定的束缚。
《阮玲玉》中玲玉绝笔的段落,那些循环往复的、期期艾艾的语调,很难令人相信“一死了之”并非是为了逃避:在影片中,阮玲玉在妇女节前的午夜与世诀别,没能把“自己的软弱、虚荣心、喜欢、苟延残喘都掏干净”。她的选择,在送别同学瑞贞时的低眉垂目我们便已了然。
阮玲玉之死后世有着诸多争议,其实无非是关于“旧女性”抑或“新女性”。而张曼玉饰演的自己对阮玲玉的自尽做出评判,即便她能够体认“人言可畏”,然而她却认为她至少会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姿态,结束生命是为了自己而非为了别的什么。这是时代的变化在女性身上划下的痕迹。
由此,关锦鹏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双重的对于身份的探寻,另一重则是影片中女性形象看待周遭世界的眼光。这样的眼光是通过身体政治而进行书写的。
在拉康和萨特的观念中,观看是“充满自信地把人置于视觉的中心”。从《女人心》《地下情》《人在纽约》,到《胭脂扣》《阮玲玉》,镜子作为重要的意象不断地在四处流散,它成为女性不断进行自我体认的通道,女性在凝视自我的过程中完成了身份的推翻与重建。
在他的影片中,女性总是长时间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有时梳妆,有时摆弄身姿,更有时只是如同赵淑珍前后两次的微微抿起嘴角而已——前因后果语焉不详,这是属于她望向自我深处的时间与空间,不足为外人道。而在阮玲玉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坐在镜子之前,终于能够写下那些她的言不由衷。与其说是写给他人的讯息,不如说是生命的自白。
而当两性身处同一空间之时,即是视觉权力受到威胁之时。不论是一对不能够在一起生活的情侣,或是在男导演与女演员之间——关锦鹏会借助镜像打破叙事轴线的原则,使得两张面孔同时面对镜头——知觉的链条断裂,在影片的符码中,则呈现为两者观看的“失焦”。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关锦鹏总是偏爱在影片中设计数位女性,并且将她们之间的关系刻画得矜持且暧昧。在他的短片《两个女人,一个靓,一个唔靓》中,更加得以通过极其先锋的笔法清晰可见:她们对坐在桌前,望向彼此,却在脑海中心照不宣地构建了一个游乐园似的的舞台。从这个角度上说,女性是彼此的照镜。
于是我们终于能够回到关锦鹏在《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中向谢晋提出的问题:拍女性电影拍得好的,是怎样的一些人?
电影是文本和图像的游戏,同样,它也不断生产、加强、消费着性别固化和社会角色的观念。当我们认为关锦鹏是一位“女性电影”导演之时,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故事都围绕着女性发生,反而恰恰在于他并未提供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论述:女性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成为男性,而是成为自己。
关锦鹏的电影是“热烈”的反面,真实,但也疏离得远。他从不曾给予任何答案,而总是选择在镜头的远处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框出了望向女性的一个缺口,有光亮照射进来,也通往着另一个银幕之外的、更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