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弥坚的战士: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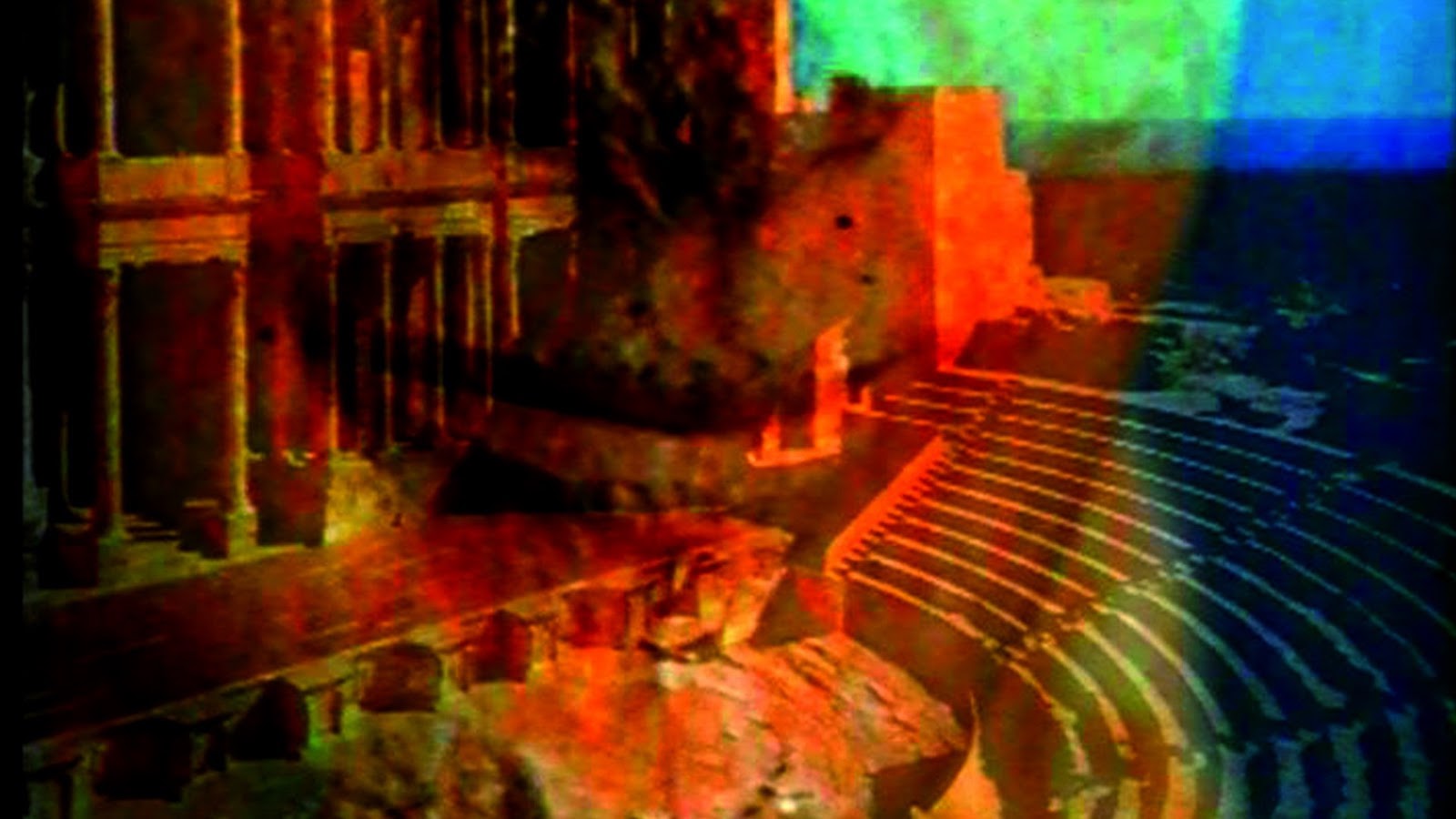


半个多世纪前,让-吕克·戈达尔执导的电影《筋疲力尽》(Breathless),一夜之间,将其推上了世界电影舞台的风口浪尖。今年,他又向世界影坛带来了一部极富政治色彩的,诗文化实验电影——《电影社会主义》(Film Socialisme,2010)。戈达尔就好像一个老而弥坚的老兵,一直战斗在“何谓电影基准”的前线阵地。《视与听》(Sight & Sound)杂志特约撰稿人Gabe Klinger试图通过“跳切式”的文本分析,结合这部电影,描摹这位左翼电影导演生命中的吉光片羽。
2010年6月18日
巴黎,“制作电影”(Cinéma des Cinéastes)论坛,《电影社会主义》映毕之后,久违影坛的泰斗,79岁的让-吕克·戈达尔,现身现场。戈达尔习惯性地点上了一根雪茄。立马,现场主持人Edwy Plenel提醒观众:“戈达尔先生可以抽烟,你们不行。”正是这个小细节,提醒我们,戈达尔是一位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贵宾”。同时,法国新浪潮的杰出代表吕克·慕莱(Luc Moullet)、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和让·杜歇(Jean Douchet),均有出席。现场溢满了崇敬的气氛。若在很久以前,戈达尔出现在电影院,观众们是要脱帽致敬的。
戈达尔的电影,好像一个个体,在过去的半世纪里,经久不衰地占据着评论高地。就在《电影社会主义》揭开面纱的前夜,恰逢《筋疲力尽》(Breathless)公映50周年纪念日。试想,一个从未接触过戈达尔那浩瀚如海般电影作品的观众,在看了《电影社会主义》之后,他绝对估不到,这部电影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者制作的。意赅地说,《电影社会主义》是一部大胆结合数字美学(digital aesthetics)的,非传统的叙事散文/诗(essay-narrative-poem)电影。这是一个特殊的夜晚,戈达尔亲临现场,与观众海侃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其间频频妙语连珠……
三个月前,戈达尔以“希腊问题”(problems of the Greek type)作为缘由,拒绝出席《电影社会主义》在戛纳的首映礼。于是,一干“伤不起”的记者团,开始就此事,大做文章。他们将戈达尔的个人态度与他的电影《电影社会主义》进行了奇异的互文感知——他的电影跟他的为人一样,目空一切。常居巴黎的戈达尔迅速做出回应:我的话,一直很容易招来攻击。这点,我比你们更伤不起。反正,我从来不故弄玄虚,居高临下地戏弄或者讥笑电影院里那些热情的听众。
如此一来,火药味十足的舆论环境,使得《电影社会主义》在戛纳获得的评价,草率有余,分析不足。吊诡的是,关于这部电影本身的辩论,又是极具开放性的。具体地说,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对人类历史进行了一次高浓度的“压缩”——从青铜时代到西班牙内战,乃至当下的经济危机,等等。若没有做足功夫,要对这部电影进行“解压”是很困难的。(功课完全纲要请见《S&S》2011年8月刊登的Brad Steven的评论文章)事实上,对于那些不熟悉戈达尔电影特有的脱节风格(disjointed style)的观众来说,这类散文电影可以参照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让-丹尼尔·波莱(Jean-Daniel Pollet)以及阿涅斯·瓦尔达的作品来佐证。或者,从二十世纪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宏大的角度来说,《电影社会主义》又显得深不可测。
1950年9月3日
很少有人知道,长年泡在电影院的让-吕克·戈达尔,从19岁开始便定期为《电影公报》(Gazette du cinéma)供稿。期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迈向政治电影》(Towards a Political Cinema)的文章。这篇文章成为了戈达尔电影理论之“政治面对电影”的最早证据。文中,戈达尔谈到了他对于新闻短片《五一》(May Day,高蒙公司出品)的见解。通过这个短片,戈达尔意识到了电影作为政治宣传的巨大影响力。他眼看着,那些芳华正茂的德国共产党员,被那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画面所打动,将自己投身到那所谓的更伟大的事业中去。类似这样的文章,常常出现在戈达尔电影生涯的早期。戈达尔在文章中指责了那些“不幸的法国电影制片人”(unhappy filmmakers of France)。因为,他们并没有制作出议题主导电影(issue-oriented films)。这些文章,使得戈达尔看上去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挑衅者。
换句话说,与戈达尔同代的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或者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从未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表示过自己的政治立场。当时,他们都是《电影公报》(稍后的《电影手册》)的主力写手。相反,戈达尔的文章总是与当下的时政时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第二部长片电影《小兵》(Le Petit Soldat,1960)便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叙事背景。六〇年代末,戈达尔更是制作了大量的,政治色彩浓重的电影。其中,尤以《中国姑娘》(La Chinoise,1967)和《远离越南》(Loin du Vietnam,1967)为杰出代表。曾几何时,戈达尔说过,“新浪潮被某些人指责为一无是处,只会拍人在床上(people in bed)的镜头。” 这项“指控”我们可以引申到戈达尔的成名作《精疲力尽》。片中最长的一个叙事段落,正是两位主人公窝在床上,争论不休。然后,戈达尔紧接着说道:“我的角色都是在政治方面很活跃的人物。有时间上床争论,没时间上床睡觉。”
1956年4月26日
1956年4月26日,戛纳组委会综合了西德方面的压力,以及某地方上的被驱逐囚犯协会的要挟(你们要不放这部电影,我们就占领你们的放映室),昭告天下,《夜与雾》将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影片,放映。作为首批解析纳粹集中营恐怖阴影的电影之一,《夜与雾》的公映好像一剂强心针,将散文电影浇铸成了一种亚类型电影。同时,阿伦·雷乃以极高素养的美学追求,搭配重大历史题材,再度确立了电影作为一种纪录历史的宣传工具。
不像之前的纪录片,《夜与雾》是一部由专业团队拍摄的,融合了原始素材(当时的集中营画面)和现时物料的电影。另外,大屠杀的幸存者,小说家Jean Cayrol创作的剧本,更是为电影提供了激荡人心的动机议程:历史不能再度重复。与此同时,戈达尔开始着手制作一部名为《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ema(1989-98)的电影。戈达尔试图利用影像历史,全面地内化雷乃与Cayrol的美学追求以及心灵悲歌。《电影史》由八部分组成,融汇了戈达尔对于艺术史、全球政治以及电影,三者之间的潜心聚焦。为使观众们能同步理解,戈达尔宣称:“你们在广岛……在萨拉热窝……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戈达尔利用影像历史学,对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做了一个全面回顾。
1993年的精妙杰作《向萨拉热窝致敬》(Je vous salue, Sarajevo)时长仅两分钟,以解构波黑战争中一张照片为主,戈达尔亲自为电影作画外音。他的旁白,不仅充满了诗意,更为影片做了扼要的综合性陈述——“有规则,也有例外。”戈达尔告知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规则:香烟,电脑,T恤,电视机,旅游业以及战争。但是,没有人去谈例外。反观,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此著书立传;格什温、莫扎特为此谱写华章;塞尚、维梅尔为此挥毫泼墨;安东尼奥尼,维果为此燃烧胶片。”
在《电影社会主义》中,“规则”是电影第一部分的主体:一艘巨大的观光巡游轮船沿着人类文明的摇篮(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逡巡,然后驶入欧洲(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其间非常理地取道黑海(乌克兰)。角色们穿梭于健身房,赌场,餐厅,夜店,低档的艺术画廊,甚至一个老虎机旁的类似于基督徒临时祈祷室的地方。显然,对于戈达尔来说,“规则”是人类登陆每块新大陆后,肆意挥霍留下的碎屑。
与压抑的,现实中的游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例外”:人类曾经取得的,那惊鸿一瞥般存在过的荣耀(也包含人类犯下的一些极其愚蠢的行为)。这些部分以电影片段,绘画,古典音乐和文学作品,互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这也是戈达尔上世纪七〇年代中期开始在层出不穷,分门别类的影像随笔中所提到的“核心材料”。戈达尔的类型混合最终使得《电影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整体:《电影社会主义》的三段,没有一段因体裁特殊而与其他段落格格不入。戈达尔的叙事完全被随笔般脱离主线的“离题”所丰盈。这种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其实早就出现在乔伊斯(Joyce)和贝克特(Beckett)等人书写的文学作品中。反观,二十世纪的电影,无人问津。有意思的是,《电影社会主义》巧妙地将日趋成熟的电影散文形式与新兴的,以数码传播方式形成的视觉文化,交相辉映。
1905年6月14日
这个日子,是与《电影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相关性的一个日子。这天,沙皇俄国的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发生了军变。这一事件成为了谢尔盖·爱森斯坦1925年虚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的原型。这部电影所引申出的“概念”,恰恰为戈达尔的《电影社会主义》和《电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提供了某种样品模型。这个概念就是,影片的戏剧修养将构建在一个对真实事件的记忆进行扭曲或替代的叙事模型上。反而,电影制作者并不会对真实事件本身太过感兴趣。
戈达尔在他1950年的文章中,引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的话写道,“这种自我意识的表现形式,揭示了艺术家是如何‘通过自发的、富有激情的诗意事件,参与到历史情节剧之中’。”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爱森斯坦以视觉化形式所表现的“敖德萨阶梯”,更为人津津乐道。因为,爱森斯坦更为有条不紊地重组了当时的叛变事件。戈达尔正是在他的那些视频散文式电影中,以反复地除去现实中的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元素(事件),实现巴赞的电影理念。
然而,戈达尔也受到一部较早期散文电影的暗示。这部电影就是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于1993年执导的影片《最后的布尔什维克》(The Last Bolshevik)。影片以电影制作者亚历山大·梅德韦德金(Alexandr Medvedkin)的生活为蓝本,通过电影作为国家宣传机器为切入点,研究苏联历史。其中,克利斯·马克向观众上演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叙事段落。他人工测量了“敖德萨阶梯”的物理长度。若有人在现实生活中,走上这么一段阶梯,只要短短几分钟。爱森斯坦则在《战舰波将金号》中将这一最为著名的叙事段落,通过交替剪辑,延展观众心里的叙事时间(放大现实时间),以取得巨大的戏剧效果。退一步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观察。但是,诸如克利斯·马克之类的知性电影散文家,他们懂得怎样着重抓住一个细节,让观众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转变到一种主动探索模式。随后,观众便会自我意识地对每一个后续的影像,进行审视、细察。
就像马克一样,戈达尔未曾想要“故意操纵”观众。恰恰相反,他只是将每个场景,每个历史性事件的细节呈现出来。这些细节,仿佛一个个零部件,自觉地组合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机体。这种拼接式的风格就像破镜重圆一样试图接近历史真相。尤为引人瞩目的是,戈达尔在这种诗意而壮丽的印象派概念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美学诉求。尽管戈达尔的政治立场,有时候会给人带来某种说教式的效果,显得十分迂腐。但是,其电影的表现手法从来就不是学院派的。譬如这部《电影社会主义》。对于戈达尔的贬低者来说,看这部电影就好像经历了一场令人丧气的“斯芬克斯之谜”(cryptic)。
1963年10月29日
一言堂并不是戈达尔的专长。他的电影也许在风格上很是自信,但是它们多聚焦于模棱两可的灰色地带,并且捍卫个体自由凌驾国家利益。[有这样一句口号出现在《电影社会主义》之中:“国家的理想是大一统(to be one),个人的夙愿是灵肉分离(to be two)。”]1963年秋,经过整整三年 (1960年至1963年,戈达尔还拍了四部电影),在针对《小兵》Le Petit Soldat中具有争议的酷刑场景的审查告一段落之后,这部电影才得以进入巴黎的电影院。要知道,这部电影创造了两个第一。它是继《筋疲力尽》之后,戈达尔的第一部长片;它也是戈达尔第一部潜心于政治舞台的电影。
在《小兵》中,戈达尔创造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角色——米歇尔·索博(Michel Subor)饰演的Bruno Forestier,一个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被捕的法国右翼恐怖组织成员。戈达尔反复地通过这个角色的画外音和他那种似是而非的行动(而非暗示利己主义),表现这一角色的内心疑惑。《电影手册》的批评家让-路易·科莫利(Jean-Louis Comolli)尖锐地指出:“Forestier为了寻找自我,就必须不断地从现成的解决方案中抽逃出来。他的‘朋友’与他的‘敌人’,被双向制约。矛盾始终围绕着他。假设,这个小兵是在一个纯粹的语境里独自为战。作为观众,便会在视点上或政治立场上确定他们自己是反党的。这时候,观众就会将他们自己与电影中的恐怖分子设定在同一层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只能自己审判自己。”可以说,戈达尔将自己的一部分抽调给了Bruno Forestier。因为,戈达尔从不会肆无忌惮地以纯粹的政治术语来说服别人。在《电影社会主义》中,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国”(State of Palestine)叠置于(superimposed over)希伯来文的“巴勒斯坦”(Palestine,巴勒斯坦的辞源是希伯来语)。这个称号,对于那些不说这两种语言的人来说,可谓暗码。若从说教视角对其进行解码的话,如此设计,几乎简单到不费吹灰之力。
1970年9月
最终,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这部电影窥探到戈达尔的政治偏见吗?其实,大量的真实事件被那些评论家们忽视了。显然,他们更愿意将戈达尔视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激进分子或一个脾气暴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anti-Zionist)。相对而言,他们更愿意抓住戈达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所表现出的张扬个性,而非其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政治观点。
1969年,经由阿拉法特-法塔赫党(Arafat’s Fatah party)的官方电影制片人Hany Jawhariyya,戈达尔与联合导演让-皮埃尔·高兰(Jean-Pierre Gorin)以及摄影师Armand Marco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取得了联系,从而保证他们能够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黎巴嫩,拍摄一部电影。戈达尔一头扎进了政治电影阵营之中。当时,他加入了“吉加·维尔托夫(Dziga-Vertov)导演小组”。这个小组旨重新定义政治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方法。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提议是,让这三位电影制作者远离他们的舒适地带。戈达尔、高兰以及Marco,三个人在历时了将近九个月的中东之旅之后,积累了大概四十多个小时的样片。1970年8月末,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地开始制作一部前所未有的野心之作的时候,“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爆发了。
黑色九月包括了一系列事件:一连串的劫机事件之后,紧随而来的约旦政府对那些巴勒斯坦组织的野蛮镇压。
另一方面,戈达尔和高兰也就拍摄结果陷入了困境,两个人整天吵架。他们发现,他们对这部暂名为《直至胜利》(Until Victory)的电影的整体构思,存在歧义。各种环境恶劣的外景地,最棘手的翻译问题(三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会说阿拉伯语)和各种文化差异(譬如:营地里的妇女自己教自己读写,但是拒绝了摄制组对其进行拍摄。以及更多的使得戈达尔和高兰困惑不已的问题),深深地挫败了他们。
近日出版的《戈达尔传》(Godard: biographie)[作者:安东尼·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一书,披露了当时戈达尔与亚瑟·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一次简短会晤。很显然,在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告诉戈达尔“明天再来”之前,戈达尔只问出了两个问题。不过,我们能从这两个问题里看出戈达尔对历史的多维度理解。戈达尔试图将巴勒斯坦人在上世纪六〇至七〇年代的内战,以及二战期间的犹太人战争,归纳到哲学层面来思考。
“我问他,巴勒斯坦死结问题 (Palestinians’ difficulties)的起源是不是和集中营有关,”戈达尔说道,“阿拉法特对我说,‘不,那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故事。’然后我说:‘不尽然吧,你知道在集中营里,当一个犹太犯人虚弱至极,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称他为穆斯林(musulman)。’他的反应是:‘那又怎样?’我说:‘他们可以称他为黑鬼,或者一些全然不同的称谓,但是没有,他们称他穆斯林,这表现了巴勒斯坦难题和集中营的直接关系。’”在阿拉法特提前结束访谈之前,戈达尔还问了一些关于当地习俗的问题。(原作者提供这件趣闻轶事的细枝末节,是为了佐证大量言之凿凿歇斯底里指责戈达尔是个反犹主义(anti-Semitic)的好事者,是被某一小撮不安好心的人误导的。《电影社会主义》便微妙地展现了戈达尔理解下的以巴局势。)
这些事件,犹如火上加油,更加加剧了戈达尔与高兰之间的矛盾冲突。借引安东尼·德·巴克的话说,“两者矛盾的聚焦是:《直至胜利》到底是作为一部政宣片而存在,还是作为一部以批判法展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影像教材而存在?”
1970年九月中旬,戈达尔在片中拍到的大量人物,都被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军队以屠杀、囚禁或驱逐的方式抹去了。之所以这么做,他们就是为了极力抹去——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是来自约旦的真相。当时,这群电影制作者还祈望向人们展映这部电影的初剪版,事后看来,不啻为一场悲剧。
整个九月,出于安全的考虑,戈达尔和高兰都被困在剪辑室中。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成为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Mossad),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或者约旦秘密特务机关的目标。这些周遭变故,动摇了戈达尔的核心地位。“吉加·维尔托夫导演小组”的分崩离析,不可避免。(稍后的1976年,《直至胜利》的素材在安-玛莉·米耶维勒(Anne-Marie Miéville)的协助下,变成了《此处与彼处》(Ici et ailleurs),这是戈达尔最佳电影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震撼人心的散文电影之一。)
2010年5月17日
《电影社会主义》在戛纳首映。当戈达尔的巡航班轮试图停靠巴勒斯坦码头时,银幕上出现了“拒绝访问”(ACCESS DENIED)的几个大字。此前一天,激进主义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被禁止进入以色列。身为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以色列初期是作为一名基布兹成员(Kibbutz member)活跃于社会各界的。真可谓,小小巧合,大大讽刺。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如火如荼地在中东盛开(某某花,你懂的);西班牙继希腊之后,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意大利政府面临日剧增长的监察管制;法国严令禁止穿着布尔卡(burkas,一种蒙住全身的长袍),这是右翼势力掀起的诸多令人震惊的浪潮中的一股。《电影社会主义》中的每一格画面,似乎每天都在现实生活中活灵活现地“再现”、“蔓延”。戈达尔电影的“碎镜重圆”法则在现实的日光之下,不断重组,并折射出得意洋洋的光芒。这束光芒,必将持久的,盛开在那些愿意开眼,愿意倾听,愿意亲身参与其中的人的心中。
|出自Sight & Sound 2011年八月刊|翻译:小胖纸方枪枪 | 校对:仁直



View Comments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