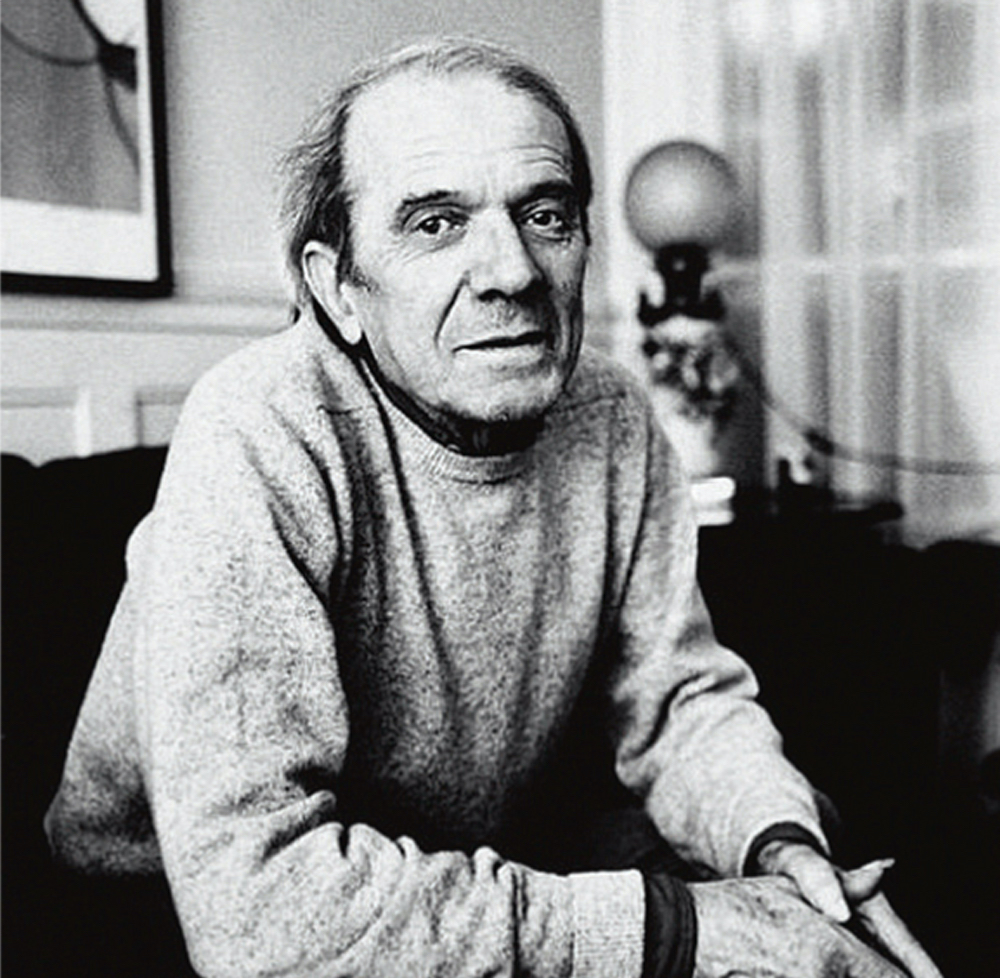
作者:特米奴加•切夫诺娃(Temenuga Trifonova)
译者:廖鸿飞 (本文已发表于《独立评论》2012年第2期)
萨特的《想象》(Imagination)与《想象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对于哲学在超越人类的思想更新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将主体性虚无化,回到对客体彼此之间变化的纯粹的知觉,而不是赋予某个影像以特权或者以其为参照中心(意识)。在萨特之前,柏格森已经对纯粹经验(非人的)感兴趣,“它高于以我们的实用性为向度的决定性的转换,这种实用性使经验变得更切近于人类的经验”(德勒兹,《柏格森主义》,第27页)。德勒兹肯定,人类的智性就是会将差异缩减为程度上的差异,而前者只能通过直觉对经验条件的考察中,通过“超越这个转换”(above the turn)而重新被发现。
为了向非人或超人(那些低于或高于我们自身的绵延)敞开,超越人类的状况:这就是哲学的意义,迄今为止我们的状况将我们的生活禁锢在被糟糕地分析的复合物之中,而我们又用这种糟糕的分析构成了我们自身。(同上,第28页)
德勒兹在两卷《电影》中的任务就是去展示现代电影如何特别地通过废除主体性而制造了超越人类状况的可能性,这种主体性在柏格森所说的“累积影像”(the aggregate of images)(物质世界)之中是一种具有特权的影像。
柏格森的绵延(duration, durée)理论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知觉和记忆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似曾相识”(déjà vu)现象的分析基础上,他认为这就是我们精神生活真实属性的最真实的表达:过去自动地保存在现在之中。同样地,德勒兹在他的两卷论电影的著作之中进一步假设时间-影像在电影(准确地说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之中的出现揭示了时间的真实属性:时间不断地分岔为不可能的现在和无须真实的过去。时间-影像被体验为过去,但是它们属于一种非人的而不是个体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影像就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形式。在似曾相识之中,我们经验到某些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然而我们却不能在我们的过去之中追寻它们,就如同我们自身的记忆已经被偷走了一样,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想起的是别人的记忆。柏格森和德勒兹都将主体作为我们整个精神生活的减缩和并且这种减缩是有必要的。为了恢复我们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们相信主体性应该被压制或超越,这反过来又呼吁一种对表象(再现, representation)的重新定义。
德勒兹的《电影1:运动-影像》与《电影2:时间-影像》回溯了电影从以运动-影像为主导到现代电影的时间-影像之间的转变,以此例证了我们对表象的理解的转变。在运动-影像的体系之下,时间是从属于运动的:事物和事件决定着心理的绵延。对于德勒兹来说,运动-影像的缺点在于它不能表现绵延,而是将其从属于运动或空间化的时间。德勒兹的观点是,现代电影已经将其自身从主体性或表象之下解放出来了,然而,他的时间-影像理论并不去除主体性,而只是重构客体的概念。客体对于德勒兹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影像,一个净化了任何物质性的,不再从属于感官-运动机制的“精神-影像”。
德勒兹相信,为了恢复存在物的原初属性而非将其作为知识的客体,主体必须变得更加主观性:它必须将其自身建构于其自身任何的表象之上,它必须创造超-表象(hyper-representation)。德勒兹将时间-影像置于运动-影像之上,是因为前者在表象之外建构自身,因而重申了主体的自主性。将运动从属于时间到达了这样的效果:绵延规定着何事正在发生,而不是事件决定着时间,主体从世界之中恢复了它的独立性。当对世界的表象仍然假设一种事物和它们的描述之间的差异之时,时间-影像清除了这种差异,代之以对事物自身的描述。
德勒兹建立起来的事物和它们的描述之间的联系类似于鲍德里亚假定的客体和符号之间联系。正如鲍德里亚那样,德勒兹似乎相信简单地将对某物的描述置于某物通常占据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位于表象的系统之中)之中,会引发纯粹的描述和类事物(thing-like)。德勒兹主张,所有的指涉性物质、所有的客体性都要被时间-影像来估量,准确地说是因为时间-影像不是一种主体性的表象,而是某物本身,一种纯粹的表达。这也是因为一个客体的理念总是假设一个主体的理念(表象不只是作为一个反思的主体的世界的表象,而且在一个对等的程度上,也是主体自身的客体化),并且表象的终极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同时虚无化。然而,德勒兹没有考虑到将表象推至终结的这个行为本身不能够被悬置。主体的某种东西仍然残留着,并且正是因为这种主体性的残留,所以将主体性推至终结的同时,这种行为又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这种视点的不可能被消除性,同样适用于文学和电影。在《小说与电影:两种类型的论文》(Novel and Film: Essays in Two Genres)之中,布鲁斯•莫里赛特(Bruce Morrissette)出色地描述了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作品之中的这种不可能性的例子。就拿罗伯-格里耶的案例来说,这个例子就是试图去除特定的、处境化的视点并且用“地理学与可见视角”(第45页)来建构它,尽管是以有一点变形的形式,莫里赛特还是展示了这个工程如何最终地恢复了叙事者的全知视角。
有可能从理性或者同一个视角的内在的合理性出发将视点与自身分离开来,就像安置一个摄影机的客观性或一双作者的眼睛那样吗?对于罗伯-格里耶来说,这种“观察者”……不能作为叙事之中的一个“角色”,他有任意地将自己置于任何位置的特权吗?……他能够以自己的意志来重置自己吗?再一次地,假如这双眼睛不是知觉上全知的和像上帝之眼那样全知全能的,那么什么东西将要阻止这样的摄影机之眼或者小说家去变成一双“同时无所不在”的眼睛?……一个全知的光学系统显然是被创造出来的,对于一个全知的作者来说,将它合理化显然是困难的或者是武断的。(《小说与电影:两种类型的论文》,第46页)
在视点的客观化和由此导致的所谓“非人化”之间,有个界限必须明确。在电影或小说之中,压制或掩饰客观性的视点从来就不能达到对主观性的完全废除。罗伯-格里耶表面上客观的视点并不必然妨碍他的作品是人文主义的小说。他对客体和事件的描述只是创造了一个表面上的非人的作品,因为它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提供‘图像’或者幼稚的现实主义意图;它们是……毋宁说一种心照不宣的心理学的支持者或客观联系物”(同上,第93页)。最“客观”的描述和对视点的操作因此仍然是“假-客观的”(同上,第106页)。
德勒兹在《电影2:时间-影像》之中的大多数观点都在重复并且时常地阐述罗伯-格里耶写于五六十年代的对新小说的分析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入《为了新小说:论虚构》( For a New Novel: Essay on Fiction (1965))。例如,当罗伯-格里耶将注意力转移到在现代小说和电影中作为意指的区分的“描述”的角色来的时候,德勒兹将时间-影像的电影描述为一种“纯粹的表达”;对罗伯-格里耶来说,“虚假”就是没有表现出“自然”,因而被从意指和逼真性之中孤立出来(第163页),德勒兹却认为当代电影中时间的真实属性就是虚构性。罗伯-格里耶提议说,正是拒绝意指和将注意力从绝然存在的事物和人类之中抽离出来(避免将世界人化),因此现代小说和电影并不去除人,而是到达了其反面:它们使人意识到他和他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真实距离。越少以人类学为中心的小说/电影,就越是真实。罗伯-格里耶将这解释为:这不是一个去除主体性的问题,而是去除决定着主体性理念的一种内部/外部之间的对立。精神内容的客观化,比如将想象和记忆作为一种物理现实来处理,就是现实主义的终极形式,因为它最终承认那种总是已经被祛除的、仅仅作为“主观视点”的东西作为现实。与德勒兹不同,罗伯-格里耶非常清楚“完全非人的观察”(第18页)是不可能的,尽管对他的小说的最常见的批评就是据说它们总是有一种“非人化的”或“中立”的属性。
即使很多客体都是被小心翼翼地呈现或描述的,但是总是存在一双观看它们的眼睛和专门地重估它们的思想以及将它们扭曲的激情。我小说中的客体从不在人类的知觉、现实或想象之外呈现。(罗伯-格里耶,第137页)
与那些对新小说的批评相反,“新小说【和德勒兹在《电影2》中讨论的时间-影像的电影,作者加上】的目的仅仅在于一种完全的主观性”。(第138页)
在第二卷《电影》快要结尾的之处,德勒兹认为电影能够并且应该被看做普遍意义上意指的可能性条件,因为电影向我们提供了进入存在的方式,它在人类知觉或意识的诞生之前就重构了世界的黎明。电影不是语言。德勒兹坚持说对于电影中的景框最贴切的比喻“是在一个信息系统而不是一个语言系统中发现它。因素【景框之中】就是数据……它们有时是不可数的,有时候是可数的有限数目。因此景框与两种倾向是不能分离的:倾向于饱和或倾向稀缺”(电影1, 第12页)。一个信息系统是前人类的、中立的、前语言的,因此作为信息或数据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比意指或符号要古老得多。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逆转:尽管在经验上,信息系统比意指或语言要“年轻”(我们总是将“信息系统”作为新近的东西),它们看上去已经超越了某种特定的“人道主义”或“主体性”,现在被回溯地认定为超越意指的或具有“非人”的特征的。这种姿态其实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因为我们不能掌握人类是如何地进化成某种东西的,所以它是异于人类的纯粹信息,对这个现象我们能够相信的唯一的回应就是假设非人的东西就是前人类的,人类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化的。这让我们能够继续相信我们仍然存在于这个人类的宇宙当中。德勒兹认为电影揭示了世界的前人类状态,就是出于这种将其保持为人类世界的欲望。他宣称,不同于总是建基于一个固定和有特权的视点(也就是主体的)因而限制我们实际的兴趣的自然感知,电影化的感知本质上就是反中心的。这个问题在于德勒兹是否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主体“去除”它自身的能力,即在于时间-影像的电影是否满足了主体性自我废除的欲望。
在《电影1》之中德勒兹将镜头作为一种意识,它比单纯的知觉意识更包罗广泛和不偏不倚,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是纯粹的影像而非在影像之流之中的选辑。虽然柏格森认为有必要从纯粹知觉“缩减”为自然知觉和电影化知觉,德勒兹却认为电影化知觉相对自然知觉而言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前者“没有一个锚定的中心和视野”(电影1,第58页)。即使我们假设完美的镜头能够拒绝固定在某一点上,总是在游走而产生不同的视野,但是镜头真的没有一个锚定的中心吗?显然,正如人类的知觉需要时间去“游览”一个客体一样,镜头也是围绕一个客体运动而不是把视点设置于客体“内部”。德勒兹想说,为了“重新发现作为其自身的、作为纯粹去中心的、作为原初的变化的、作为其自身的光和热的,但是仍然未受无法决定的中心的影响的”(电影1,第66页)矩阵或运动-影像,人类的目光能够从电影化的知觉之中被除去。然而,他被迫去认识到不可能真正地“恢复”一种纯粹知觉而只有“建构”它,尽管他没有用“模拟”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它:
【人类之眼的】相对稳定正如一个接收性的器官,这意味着所有的影像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影像发生变化,总是处于和一个有特权的影像的关联之中。而且,假如镜头被当做拍摄电影的一个装置,它就是服从同样的有限制的状况的。但是电影不仅仅是镜头:它是蒙太奇。假如从人类之眼的视点出发,蒙太奇无疑是一种建构。如果从另一种眼睛的视点出发,它就不再是单一的了,它是一双非人之眼的纯粹视野,这将是事物内部之眼。普遍的变化、普遍的互动(变调)就是塞尚所呼吁的人类之前的世界,“我们自身的黎明”,“熠熠发光的混沌”,“世界的童贞”。所以事情没什么稀奇的,我们必须去建构它,因为它只是通过我们不具备的眼睛而赋予我们的。(电影1, 第81页,作者加的斜体)
尽管蒙太奇是一个技术性的程序,它仍然是由主体、由人类之眼所控制的。宣称从“另一双眼睛”(镜头)出发的蒙太奇不是主体性的或人的,不是建构的,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者的眼睛”实际上只是另一双眼睛,而我们只有间接地通过它才能看到这个世界(人类之眼通过非人之眼-镜头来进行观看,但这并不同于镜头本身)。这对电影制作者和电影观众来说都是真实的。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条看法:镜头这种由主体发展起来的技术,比人类知觉更为“自然”或更具“物质性”。德勒兹认为物质作为运动-影像的总和不外乎是“镜头意识”,因而在人类之眼出现之前,世界就是一部电影。
假如物质是由运动-影像构成的,包含着光的变幻,这些影像并不一定需要被感知到而只是自身成为某种位于事物与表象之间的东西。电影化的影像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这样一种中介性的影像,既不是事物也不是表象【德勒兹提到,电影并不给我们如此这般的图像而只是中介性的影像,它本身已经是运动(电影1,第2页)】,它与柏格森所说的纯粹知觉(在意识诞生之前的知觉)最为类似。德勒兹跟它们客观性的程度区分了运动-影像的三种变量(variations):知觉-影像(perception-images),感受-影像(affection-image)和动作-影像(action-images)。知觉-影像是最为客观的和物质性的,因为如柏格森展示的那样,知觉是“内在于”物质之中的。感受(affection)是我们对影像的回应,但是这种回应仍然不是延展为影像上的动作。动作-影像是三种影像之中最为主观的,因为它们卷入了一个回应影像的运动机制之中。最后,时间-影像超出这三种影像之外,交还给我们纯粹的知觉。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一个系统性的缩减过程(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或一个对运动-影像的组成因素的排除而得以克服。为了产生时间-影像,我们不需要向运动-影像添加什么,而只需要破坏它或对它的三种变量(知觉、感受和动作)进行提纯。
德勒兹考虑这几种不同影像的一个问题是:当他说知觉-影像、感受-影像、动作-影像还有时间-影像的时候,他并不特别地意指电影的影像。他借用了柏格森的术语——即从自然知觉到电影化知觉的话语来移置它们,并不提供解释。他通过阐述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之间的差异,使其更为清楚。我们在对影像的习惯性识别(柏格森的习惯性记忆)之中遭遇到前者,而在自然回忆(柏格森的纯粹记忆)的过程之中遭遇到后者。运动-影像将知觉-影像延展为一种感官-运动机制的反应:不是为了感知而感知,我们以某种实用性的目的来利用我们的知觉,将影像延展为某种特定的影像之上的动作。然而,在时间-影像的案例之中我们的感知纯粹是为了感知:我们并不以动作对影像进行回应,恰好相反,我们停留在知觉或者类似的东西上,我们返回到一种有净化任何感官-运动机制必要性的知觉之中。现在,在一部电影之中显然不存在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这种区分:并非某些影像是真实的事物,而另一些则被我们感知为影像。所有的银幕上的影像都是影像。一个观察者感知银幕上的影像的时候产生的反应,显然并不像他对真实事物的反应那样。德勒兹实际上想要说,某种影像被我们感知起来就像它们是真实的事物那样,而另一些则被按照其自身所是那样被感知。尽管这样的一种区分肯定是假设的,与在日常知觉之中的这两种影像类型相对应,德勒兹并没有在电影层面上成功地解释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有什么特别之处。
运动-影像是不纯的,德勒兹这样说的意思是我们将它感知为一种别有用心的电影(有作用于其上的意图)。在运动-影像之中,银幕上的事物好像是仅作为事物出现,产生出一种幻觉:我们能够像我们向真实的和外在刺激性的事物反应那样回应它。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逆转:事物自身(运动-影像)作为一种表象或意指,因为它指涉着我们自动地识别的某种真实的客体。只有当我们建构起一种对针对事物自身的描述的时候,德勒兹认为影像变成了纯粹的表达。物质性的世界本身已经是一种意指,而我们拥有的纯粹的精神影像(我们用来代替它自身的描述)已经是纯粹的表达。对于德勒兹来说,运动-影像从属于意指的领域,因为它激起了我们的感官-运动反应,也就是说,身体是意指的终极源泉。然而,常识总是已经将意指作为某种“精神”的东西。由于柏格森的身体概念是作为某种特定的影像,所以德勒兹认为,自然感知已经是意指,影像仅仅是自身的反映,因而它们向我们呈现,我们也向它们呈现。这对于我们理解意指或表象的属性来说是一个激进的转变,因为德勒兹暗示着表象不是一种反思性意识的展示,相反,表象铭刻在知觉诞生之中。表象不是由附加的动作产生的,而是由分离的动作而产生。
假设德勒兹完全地接受了这个本质上为柏格森式的概念,他将主体批评为表象的“主人”还是很难说有什么意义。即使我们想继续使用“主人”这个词语,首先要清楚一点的是,这种主体并非有意识地表象世界,而是世界仅仅向主体呈现,世界是在“表象”自身,因为人类的知觉是有限的。相反地,当影像与身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障碍,当我们形成精神影像的时候,我们回到了纯粹的知觉,去把握其原初的光芒(luminosity)。但是将如其所是的纯粹的影像(时间-影像)等同于精神却是不对的,即便精神影像恢复了我们的纯粹知觉,即物质。物质缺乏任何潜在性 (virtuality),它不能构成时间-影像。一种时间-影像只有跟随着(或位于其上)一个运动-影像,作为其否定或者中断才是可能的。我们只有首先“偏离”纯粹的知觉,只有等它堕落为自然知觉之后,才能恢复它。一方面,时间-影像类似于萨特的影像-意识:它是对指涉物的估量,意识在其自身上坍陷,它完全地对自身透明。然而德勒兹说,时间-影像返还给我们世界的物质性。有点悖论性的是,只有通过被估量之后,物质性的世界才会被我们恢复(至少在电影化知觉上来说是如此)。
德勒兹试图清楚地主张一种关于电影化影像的本体论意义。但是,他的时间-影像的概念作为时间的直接呈现还是依赖于一种历史的或经验的分析的。尽管他在《电影1》的导言中警告过读者,他并非要提供一种电影史研究,这两卷书的中心议题——运动-影像的电影被时间-影像的电影所取代依然是建立在对特定历史性的时刻的分析基础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对毁灭性的恐怖事件无力去把握或充足地回应。时间-影像的概念相应地隐藏着伦理学的意义。纯粹视觉和听觉的电影化影像
……应该使我们抓住某些无法容忍和无法忍受的东西。……它是某种太强大的,或者太不公正的,但有时也是太美丽的东西,因此它超越了我们的感官-运动机制的能力……无论如何影像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变得太强大了。(电影2,第18页)
通过援引柏格森对知觉产生的思考,德勒兹认为运动-影像描述一种底片(clichéd),即隐喻性的或表象性的知觉:
底片就是某物的感官-运动机制的影像。正如柏格森所言,我们并不感知到某物或影像的全部,我们的感知总是比原物要少,我们只能感知到我们在感知中感兴趣的……因此我们正常地感知到的都是些底片。但是如果我们的感官-运动机制产生了障碍或被中断,那么一种不同的影像就会出现:一种纯粹视-听的影像,不包含隐喻的整个影像将带出事物自身,严格地说,以它的过剩或者恐怖或者美丽的形式出现……(电影2, 第20页)
从一方面说,时间-影像有一个严格的历史起源:没有战争它就不会产生,它的作用就是粉碎感官-运动的机制。从另一方面说,据说时间-影像在本体论意义上要优于只是作为底片的运动-影像,但是这种优越性只是一种失败(感官-运动链条障碍)的结果,这种失败既是某种历史性的特定现象,也是使我们从中收益的东西,因为它让我们以更为“真实”或者直接的方式接近物质性的现实。因为德勒兹将时间-影像看做在美学上和本体论上都要优越于运动-影像,他似乎认为应该鼓励和制造感官-运动链条的失效,虽然它只是历史上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被偶然发现的失败。只有创伤和不能言说的东西才能够改变我们关于影像是什么的看法,使我们理解这个物质性的世界是由影像所构成的。因此,一个特定的历史性事件允诺着最大限度的本体论意义,正如一个特定的电影“流派”——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应该去揭示这个物质性世界的内在的电影属性。
然而,德勒兹坚持道,我们不能在日常知觉中直接地经验时间:“我”不能经验到非时序时间,因为“我”不能除掉正常的知觉自身,不能将其排除在外,不能变得像镜头一样非人的和匿名的东西。自然知觉是有必要主体化或减缩的,而电影化知觉则是匿名的或“结晶的”(crystalline)。纯粹的视觉或听觉影像——时间-影像是一种去系列化的(de-serialized)影像,它不从任何人的视点出发,而自然的知觉-影像则是从主体的视点出发的去系列化的影像(就此而言,知觉是一种取景或去系列化)。然而,一个影像能够从一个不存在的视点出发而去系列化吗?纯粹视觉的影像的失效能够连接起那些不是从主体的视点而是从不存在的或任意的视点出发建立起来的其他影像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德勒兹所谓的“视点”是什么意思。视点一般而言指示着兴趣。从另一方面来说,时间-影像以一种漠然的方式被感知,就像它不是被我们感知到一样,或者毋宁说它是被另一个影像所感知到。
“无功利”(disinterestedness,又译为“漠然”)这个概念本质上带有康德美学判断的特点。细致地说,德勒兹的时间-影像一种纯粹的、自足的精神内容。悖论性的是,当这种新的主体性将我们带回到事物的核心,它也“不再是机制或物质性的,而是时间性的和精神性的”(电影2,第47页)。时间-影像除去感知的自然性和主观性特征(消弭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但也揭示了客体的精神性特征。时间-影像因此实现了康德归之于美学判断的调节功能:它是心灵和物质之间的一道桥梁。当德勒兹特别地提到只有纯粹的回忆(pure recollection)而非记忆-影像(memory-images)本身构成了这种新的主体性的时候,他的话语下面暗潜着的康德话语变得更加明显。这种新的主体性作为意识的扩展,是试图有意地识别的失败的结果。当我们记不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感知到的影像不能跟另一个影像连接起来,我们只是以其所是地感知它。我们想起另一个宏大的失败,那就是康德对崇高的思考中那个想象力的失败。在康德那里,想象力不能够把握绝然的巨大和崇高的客体(康德和德勒兹都没有区分知觉和想象,它们都指向经验性理解的功能),我们不能理解作为整体的客体,康德将之解释为一个间接暗示:我们被一种比我们的想象力更强大的力量所占据,这就是理性。同样地,纯粹回忆正是记忆-影像试图耗尽潜在的失败。正如整体性的概念无限地大于想象力所能够把握到的,潜在或纯粹回忆也无限地大于记忆-影像自身所能够现实化的。纯粹的影像是识别失败之后的剩余物:潜在或崇高不能在某种特定的影像之中被发现,而只能在影像之剩余或之外被发现。纯粹的影像激发出一种不安感、不确定性和不可完成性。
德勒兹的康德主义在他对柏格森的绵延的惊人解释之中也体现出来。因为他将柏格森的纯粹记忆作为一个本体论的领域,他用柏格森的绵延来建构了一种非时序的时间。在德勒兹对柏格森的阅读之中,潜在并不表达绵延,而时间则作为一种先验的直觉(直观intuition)。实际上,德勒兹认为“柏格森比他自己所想离康德更接近:康德将时间定义为内在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内在于时间。”(电影2, 第82页)。德勒兹将时间区别与存在者(being),将变化(时序)从其中去除,并且得出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论:“主体性(subjectivity)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它就是时间,它就是,灵魂或者精神,潜在。现实(the actual)总是客体性的,但是潜在是主体性的”。(同上,第82-83页)存在(时间)现在因为主体性而有了共同的边界,个体化的人类显得比主体性“更小”:我们越是从现实、从现在之中缺席,或者我们越是在回忆之中迷失自己,我们就越能够扩展自己本来的客观性,而变得越来越有主观性。这种对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主体/客体关系的颠倒,使得客观性“大于”主观性。这将我们从痛恨或害怕自己永远不够客观的情绪之中解放出来。它同样将我们从后现代主义之中解放出来,因为只要主体被确信为一个视点(尽管是局限性的和处于其他相对的视点之中的),那就依然是一个有效的立足点。然而,如果我们从德勒兹对我们总是已经作为客体的假设出发,主体性就变成了一个我们总是无法到达的不断地撤回的地平线。客体或在场现在被看做一个视点,而主体性变成了最为非人的、非人模式的意识。
为了将他的时间-影像的概念阐述为一个非人的事件,德勒兹让我们想象
……一个地球上的事件假设被传送到其他不同的星球去,其中一个是同时地接收到(以光速),但是第二个更快,第三个更慢,因而在它发生之前和之后。后者仍然未接收到,第二个已经接收到了,第一个正在接收,三种同时性的现在仍属于同一个宇宙。这就是恒星时间,一个相对性的系统,它的特点不以人类为中心而左右……这就是多元主义者的宇宙,在这里一个和同一个事件以不可并存的版本在这些不同的世界中上演。(电影2, 第102页)
德勒兹将时间-影像描述为一种恒星的或宇宙的影像,这让我们想起了鲍德里亚版本中的超真实(hyperreality)中主体,一个“轨道外的”星球,非人的主体。实际上,德勒兹的时间-影像作为一种对时间的直接呈现是与鲍德里亚的模仿时间不能区分的。然而,当鲍德里亚将超真实看做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威胁——它足以使得我们去感知到某些已经停止存在很久了的但它的潜在影像却仍然维持着的东西的时候,德勒兹则将世界的潜在化当做一种解放。鲍德里亚哀悼我们已然“被从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位置放逐,本来在那里我们是可以有耐性去将我们的事件反思到我们自身,因而是有结果的。”(霍洛克斯,《鲍德里亚导读》第10页)。因为所有的事件和我们所有的行为已经被减缩为信息,我们不再能够成为我们所做的或发生于我们之上的东西的源泉或本源了。事件和行为仅仅指涉着其他的事件和行为,而不是指涉着一个产生它们并向它们指派意义的主体。主体或者完全地消失了或者已经铭刻在一个由事件和行为组成的网络之中,在这里不再有特定的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的概念依赖于将价值归结到事物的行为,然而,在一个虚拟的(潜在的)世界之中价值的问题不再被提起)。德勒兹将主体的耻辱解释为作为事物(与其他的影像)的解放任意视点的状况,这是出于真实和一致性的需要;而鲍德里亚并不认为这种解放是可能的,他认为虽然古老的真实概念已经消失了很久,它已经被可信性(credibility)的概念所取代,但是可信性并不描述一种所有影像是“平等的”和不从属于一个中心化的、有特权的影像的状况,相反,可信性就是真实的原则变得疯狂。
德勒兹用场面(奇观spectacle)来描述纯粹视觉与听觉的影像。在现代电影之中这种情景不是延展为动作而是停留在一个纯粹视觉或听觉的描述或者对事物或角色的陈列。这种场面拥有一种影像加压的效应或意义,使其自身成为壮观的(自足的)甚至是日常的。然而,“场面”对于鲍德里亚和德勒兹来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对于前者来说,场面将壮观与超真实区分开来,而对于后者来说,壮观就是时间-影像的本性。场面摇摆于拟像的影像与作为“时间的直接呈现”的时间-影像之间。纯粹的影像是独立于主体性的,因为主体性只有作为主体与世界之关联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将对一个事物的描述代替一个事物本身并不能够建构起主体的胜利,而只能建构起它的消失。
对于鲍德里亚来说也是如此,当一个事物被它的影像所代替,影像就变得自足和独立于主体了。主体只能存在于它自身和别的东西(世界)之间的差异之中,但是只要主体将它的影像或对事物的描述投影到这些事物之上的时候,事物的深度就消失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了。无论主体从何处观看,都只能看到它自身,这意味着它不再能够看到它自身,因为观看只有在假设某物不同于被看到的某物的之后才是可能的。超真实的出现指示着主体性的消失。因此,当主体的权力看上去已经到达它的边界的时候,即事物被对它的描述或影像的时候,主体将其自身虚无化掉:一个纯粹视觉的影像独立于主体。具有悖论性的是,通过对世界的去真实化,使得作为参照物的事物消失,主体正是在建构起只要它被困于指涉和表象的系统之内它就总是缺乏的东西:一种绝对地自治的世界,它不从属主体,但将主体仅仅作为众多的潜在性中的一个。只有将世界潜在化,主体才能保证有某种东西不同于其自身,某种不能控制的高于其自身的东西。一旦真实不再是充足的(不再充分地不同于主体),而是看上去就仅仅是主体的建构,那么唯一拯救真实的办法就是使其变成超真实,去假设它拥有那种主体一直想要拥有但永远无法拥有的绝对的主权。只要主体将其自身作为一个与外部某物分离的内部(因而就是独立)的时候,真实的主权是不可能的。主体性虽然不能完全地被废除,但是总有一个主体被宣布压抑的“位置”,主体可以撤退到这里保存其自身。鲍德里亚所谓的“致命的客体”并非一个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体。致命的客体实际上是一个获得了主权的客体,一个作为纯粹表面的客体。
电影从运动-影像到时间-影像的过渡揭示了主体作为表象的代理的衰败。运动-影像仍旧属于一个表象的系统,而在现代电影之中,故事或情节则被纯粹的(非参照性的)时间-影像或纯粹(非指涉性的)的语言所取代:
因为时间-影像即将要诞生……现实的影像必须进入一种与其自身的潜在影像的关联之中;从一开始纯粹的描述必须被一分为二,“重复它的自身,重新占据自身,分岔,与自身冲突。”一个影像具有两个向度,现实与潜在,它们都必须被建构。我们不再停留在现实影像与其他的潜在影像、回忆或者梦幻的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最终还是会变成现实:这依然是一个联系模式。我们处于一个现实影像与它的潜在影像的情景之中,在这里已经不再有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任何联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不可分辨性,即一个知觉的交换状态。(电影2, 第273-275页)
通过反对对潜在的表象,德勒兹认为想象(或潜在)扩展到了主体之外。另外,因为柏格森对德勒兹关于时间作为虚构(通过虚假记忆或似曾相识的概念)这种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萨特对于这个理念的意义。萨特认为,想象的生活是可能的,因为“它不仅是非真实客体的物质性,而是所有空间的和时间的决心,借此它得以介入到这种非真实中去”(萨特《想象的心理学》第 180页)。然而在知觉中一个客体的空间的决心依赖于另一个客体的空间决心,因此,影像的可变的、空间的决心是被“内在化的”,变成了客体绝对的、不可变的性质(同上,第182页)。非真实是自我指涉的、绝对的和虚假的。影像的自我指涉组成了影像之中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不可分辨性。时间(不是被空间化的时间,因为空间化的时间总是一种指涉性的因而是可量度的东西)在本质上是自我指涉的:时间-影像不描述一种特定的事物状态,而是它自身就是事物的状态。虚构暗示着纯粹的表达:去虚构意味着不再意指/表象。德勒兹相信,虚构的叙事超越形而上学并且超越后现代主义,后者的相对主义仍然建立在关于真实的理念之上。这种叙事应该恢复没有真实的世界的原初的中立性和无意义性。德勒兹认为,虚构的叙事是元叙事及其自身的自我指涉,它向我们恢复了纯粹影像的前意指的领域。令人奇怪的是,过度的意指(自我指涉作为意指的最高限度)向我们恢复了事物的前意指状态。人们可以假设,我们越是压抑参照物并用我们对它的描述去取代它,我们就越是远离参照、现实、物质,但是德勒兹认为这个反面是正确的:因为自然知觉已然是意指,为了去解除自然知觉已经产生的一切,那么我们需要超越它去达到元知觉(时间-影像是一种元知觉,一种关于知觉本身的知觉)或者元叙事。换言之,为了恢复知觉自身原初的纯粹性,我们必须对知觉去自然化,使它尽可能地变得人工化。
如果后现代主义能够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种关于将世界归结为语言的观点,德勒兹拒绝将时间-影像看做是一种特定的符号就是一种他本人对后现代主义反感的态度。与其说时间-影像是一种表象,不如说
……它表达了“典型”,但却是在一个纯粹的独一性(singularity)、某种独特性之中进行的表达。这是符号,它就是符号的功能。但是,只要符号在运动-影像之中发现了它们的物质性,只要它们从运动的物质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表述特征,它们就处于唤起另一种综合的危险之中,因为这会令它们与语言相混淆。只有通过组合和综合或概念,对时间的表象才能够被从符号之中抽离出来……这就是感官-运动机制、抽象的代理的含混性。只有当符号直接向时间敞开的时候,当时间为其自身提供指涉性物质的时候,已经变得时间化的类型才与从其自身的组合机制之中分离出来的独一性的特征相符。(电影2, 42-43)
这让我们想起那个与柏格森对记忆与身体的思考的遭遇的悖论问题:身体(对德勒兹来说是感官-运动机制)表达了对于我们来说最典型的、抽象的和广泛的东西,然而记忆则将我们的精神生活个体化。柏格森在《创造的心灵》(The Creative Mind)中以身体对特定的外部刺激的产生类似反应来解释了普遍理念的起源。德勒兹沿袭柏格森的路子声称,运动-影像实际上不如时间-影像,因为“它将事物和在同一个平面上许多类似于它但不同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激起了同样的运动”(电影2,第45页)德勒兹的时间-影像概念将运动从属于时间,这在他关于时间思想的总体语境之中看上去有点儿奇怪和格格不入。由于德勒兹如此激情地宣称运动并不附属于物质,因为物质已经是运动因而已经是影像(运动-影像),所以现在他想要说,时间是与运动分离的,实际上它是先于运动的。当物质作为影像这个概念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打击的时候,时间作为一种先验的形式这个理念也就从物质的运动之中分离出来(并且因此从运动之中分离出来,因此物质就是运动),好像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回归。
德勒兹成功地将时间-影像与从其中出现的新的主体性并置在一起,并且超越了语言吗?这种新的主体性“不再是运动的或者物质性的,而是时间性的和精神性的:这是“附加于”物质之外的,而不是使物质的扩展;是回忆-影像而非运动-影像“。(电影2, 第 47页)。从另一方面来说,运动-影像扩展那些原先就是浓缩的物质。正如之前的柏格森和鲍德里亚那样,德勒兹采取了“膨胀”(distension)和“收缩”(concentration)来描述物质和心灵之间的关系。正如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The Perfect Crime)里面说的那样,宇宙本来就是物质的绝对收缩(热),是无否定空间的绝对的自我认同。在一个点上它逐渐地开始冷却并且这种冷却就是时间的诞生,而它在这些物质之后又创造了缝隙、空间、间隔。真实不仅仅是主体的建构产物,而是与世界的诞生同时出现的东西。对于德勒兹来说,物质与心灵之间的唯一差异就在于运动与时间-影像之间:前者指涉(即延展为运动)而后者则并不指涉。在最后的分析而言,德勒兹仍然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他将物质与心灵之间的差异还原为了一个语言上的差异(指涉)。与其说“存在一个客观的真实吗?”,他宁可说“影像如何能够同时存在于两个领域,一个是指涉的,而另一个则是非指涉的?”德勒兹假设存在客体(非指涉性的影像)和主体(指涉性的影像,它的指涉已然是自我指涉),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去区分这两者。他不问“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而问“什么样的知识存在着并且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对其产生混淆?”
德勒兹仍旧关心电影影像对于思考能做什么多于关心电影影像的特定性质。影像不再从属于主导性的美学理论,而从属于本体论。例如,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非人:时间漫谈》(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之中,影像已经一个不断地被僭越和消弭(de-limitation)的界限,这就是作为消弭的崇高。在康德与非人的(后现代的)的崇高之间的差异之中最明显的就是前者能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的扩张,而后者则最好被描述为一种存在意识的强化。扩张假定主体掌握着物质性的世界,而强化则暗示着主体“还原”到它自身的物质性或事实性。
时间-影像是一种崇高体验吗?利奥塔的崇高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式是不同于时间-影像的,尽管它们两者都被确信为时间的体验。利奥塔认为在崇高体验的时间特征的感觉(sensation)与木偶般服从的机械主义之间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相似性。使得崇高体验与自动玩偶的机械式“生命”之间类似的,正是时间的体验不是作为一系列保持 (retentions) 与预期(protentions)的一种对分离运动的综合,而仅仅是时间的发生(happening)。崇高的体验是一种“神圣的自动主义”(divine automatism),人类(或木偶)就是从这里脱离了所有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利奥塔将这种意向性作为“时间性综合的能力”(《非人:时间漫谈》,第163页)和历时性分析的基础。这种“神圣的自动主义”被利奥塔明确地解释为“相同者的自我满足”(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Same)(页码同上),这种看法强调崇高体验是一种对时间的在场(being)体验而非对时间的消逝(passing)体验。后现代的崇高假设对主体的压制,这是由于主体被定义为意向性或者时间性综合的能力。只有当主体已经被还原为木偶,只有当它自动地对外在刺激产生回应的时候,只有它完全地放弃自身的时候,只有当它的代理者已经被消除而只剩下感官-运动机制的时候,主体才能够直接地感觉到时间,而无需将其自身击碎并徒劳地对其自身的碎片予以综合。
然而,事物与德勒兹的时间-影像非常不同地并置在一起。德勒兹确实区分了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的主要差别,这个差别使得时间-影像之中感官-运动机制的中断作为主体不能够或不愿意自动地回应外在刺激、中止了所有动作并且仅仅为感知影像而感知影像的结果。对于这两个思想家来说,时间的直接体验依赖于对代理者或主体性的排除:利奥塔的木偶以纯粹机械性的方式发生作用,没有任何的主体性意向,而德勒兹则强调后现代主体无力去发生作用。因为利奥塔的主体性概念先于代理者或意向性,一旦这个消失了,主体也就消失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德勒兹认为,一个新的主体性伴随着时间-影像的出现而诞生。然而,这种新的主体性仍旧是某种自动化的或者木偶式的东西。正如德勒兹所观察到的,时间-影像的电影是一种见证者(the seer)的电影,而非行动者的电影(the doer)。当主体发生作用的能力已经被压制的时候,主体对影像的注意力就被强化了,并且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感知影像而感知影像。主体几乎就像被影像所催眠了似的。人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中,自动地、机械地、没有意向或意愿地发生动作。
在时间-影像的领域,主体不再是将其他的影像围绕其自身而进行组织的有特权的视点,因为现在其他的影像已经变成它们自身的视点。时间-影像不再是主体性的,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是时间的直接经验而非对时间的表象。因为德勒兹以动作强化了主体性,所以一旦主体被剥夺了作用于其他影像的权力,他就能够说表象已经被超越并且时间-影像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即客观的。德勒兹认为主体抹去其自身并且变成了置身于与其他客体一起的一个客体(或者置身于与其他影像一起的一个影像),这正是不将其自身客体化,即不作用于其他客体/影像之上的结果。通过从世界之中撤回,通过无力向世界做出回应,主体净化(purges)了自身。柏格森将意识或自由定义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间隔,当意识不能对外在刺激做出回应的时候,意识的生命变得更为丰富了。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的时间-影像指示着一种意识的扩张,一种人类自由的增加。然而,德勒兹并不解释人类自由的增加是如何能够被解释为影像客观性的增加和作为对世界的有特权的视点的主体的压制。这里仍然存在一个含蓄的假设,这就是主体是一个视点,而一个有特权的视点就是作为它所发生的作用。然而,即便当主体中止动作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视点。
时间-影像之中感官-运动链条的中断仍然还不是作为视点的主体性的终结。实际上,正好相反:主体越是不能够作用于其他影像,主体性就越是被强化,或者如德勒兹所承认的那样,一种新的主体性诞生了。新的主体仍然解释影像和事件,但是不再判断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这种确认的不可能性表示:不必要真实的过去不是对主体死亡的裁定,而仅仅是主体的重构。主体性不再能够被限制在真实的理念之内,因为真实是一个不断地被主体所超越的界限。根据德勒兹,成为一个对世界的视点意味着一个人能够对世界的真实性作判断。这种判断植根于动作:主体对世界真实性进行判断的能力依赖于它作用于世界的能力。然而,时间-影像已经证明主体的概念必须被重新定义-拓展,因为主体不是被它作用于世界的能力和它判断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假的能力所耗尽。因此,德勒兹对他自己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能够废除自身?”应该就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废除我们自身,我们只能拓展我们自身。
【作者简介】
特米奴加•切夫诺娃(Temenuga Trifonova),保加利亚人,电影理论家,现为美国约克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系教授,代表作有《法国哲学中的影像》(The Image in French Philosophy, 2007)和《欧洲电影理论》(European Film Theory, 2008)。
【译者简介】
廖鸿飞,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学院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