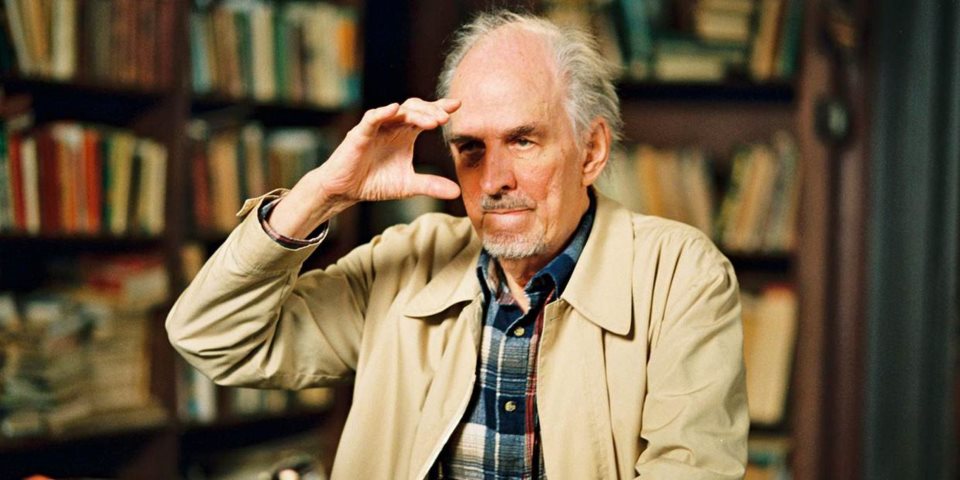
收到伯格曼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西班牙一个可爱的小镇奥维耶多(Oviedo)拍摄电影。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将这个电话信息辗转传达到了片场。伯格曼曾经告诉我,他不希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世;我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所做的只能是希望他能够得到所有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平淡无奇的天气。
我之前曾和那些对艺术家抱有浪漫主义看法并将创作视为对上帝献礼的人说过,“最终,你的艺术作品并不能拯救你。”无论你创作出多么伟大的作品(伯格曼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电影杰作片单),它们都无法使你摆脱等候敲门的宿命,一如《第七封印》结尾处骑士和他朋友们的境况。于是,在夏季的一个日子里,这位描写死亡的伟大的电影诗人伯格曼,也无法延长自己不可避免的死局;而我生命中最优秀的电影人就此离开了。
我曾开玩笑说,知识分子视艺术为天主教,那是对来生的一厢情愿。我想说的是,与其活在大众的心里,不如活在自己的公寓里。当然,伯格曼的电影还会继续存在,它们会在博物馆或电视上放映,也会以DVD的方式销售,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些都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而且我很肯定,如果能够将他的每一部电影换来他多一年的生命,他会非常开心的,这样就可以给他多六十年的时间来继续制作电影;那会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作成果啊。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会利用好这些多出来的时间继续从事他最热爱的事业:制作电影。
伯格曼很享受拍电影的过程。他不太在乎别人对他电影的评价。受到赞赏时他会很开心,但他有一次告诉我说,“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拍的电影,只会让我烦恼——大约30秒。”他对票房不太感兴趣,即使制片人和发行商打电话告诉他首映周末的票房,那也是左耳进右耳出。他说,“过了周三,他们狂热乐观的预期就会化为乌有。”他享受着评论界的赞誉,但那些并非什么必需品;虽然他也希望观众能喜欢他的电影,但他总是不会让观众轻松得享用他的电影。
不过,尝试理解的电影还是很值得尝试的。比如说,当你领悟到《沉默》(The Silence,1963)中两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互为对立的两种性格时,这部原本晦涩的电影顿时豁然开朗;如果你在观看《第七封印》和《面孔》(The Magician,1958)前对丹麦哲学有所了解的话,那也会很有帮助,但他作为一个叙事者的天赋如此惊人,以至于他能够用那些晦涩难懂的素材吸引住观众,让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我听见观众在看过他某部电影出来后说,“我没有完全明白刚才看到的东西,但每一帧都吸引着我,让我无法离开。”
伯格曼热爱戏剧事业,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舞台导演,但他的电影作品并不只是受到戏剧的启发,他还借鉴了绘画、音乐、文学和哲学。他的作品探究了人类最深层的关注点,并且经他的生辉妙手,将这些电影诗歌演绎得隽永深远。死亡、爱情、艺术、上帝的沉默、人际关系的困扰、宗教怀疑的痛苦、失败的婚姻、人们无法沟通的无奈。

然而这个男人也是一个热情、风趣、爱开玩笑的人,他对自己的伟大天赋缺乏信心,沉迷于与女性厮守的时光。和他相遇并不是突然进入一个强大的、令人生畏的、黑暗的、陷于沉思天才的创作殿堂,而这位天才正在其中用瑞典口音讲述着关于人类在阴暗宇宙中可怕命运的复杂见解。和他交流的情形更像是:“伍迪,我做了一个愚蠢的梦,梦见我在片场拍电影的时候不知道该把摄影机摆放在哪里了;关键是,我知道自己对这个很在行,而且我已经从事了很多年了。你有没有做过这种让你紧张的梦?”或者会是,“你觉得拍这样拍电影会不会很有趣:让摄影机一动不动放着,就让演员在画面里进进出出?人们会为此笑话我吗?” 如何在电话中回复这样的一位天才呢?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他做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呈现特别的效果。毕竟,他发明的探究演员心理深度的词汇,在那些以正统方式学习电影制作的人听来也会觉得极为荒谬。在电影学校(我在50年代曾在纽约大学读电影专业学习,不过很快就被赶了出来)里,强调的永远都是移动。学生们被教导说,这些是移动的画面,摄影机应该移动。老师们说的没错。但伯格曼会把镜头聚焦于丽芙·乌尔曼(Liv Ullmann)或碧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的脸上,然后把它放在那里,不再移动,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因他卓越才华所特有的独特而奇妙的事情就会悄然而现。人们会沉浸在角色中,不是百无聊赖,而是激动颤栗的。
尽管伯格曼有着自己的怪癖、以及对宗教和哲学的痴迷,但他是一个天生编故事的人,即使他满脑子是如何戏剧化尼采或克尔凯格尔的哲学,他还是忍不住享受娱乐。我经常和他进行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他希望将会谈安排在他居住的那个小岛上,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来访邀请,因为我讨厌长途飞行,也不喜欢乘坐小飞机去靠近俄罗斯的某个小岛上享受预想中的酸奶午餐。我们总是在讨论电影,我也会让他说得更多一些,因为我觉得光听他的想法和点子就让我受益匪浅。他每天都为自己放映电影,从不厌倦。
就像所有伟大的电影风格家一样,比如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和布努埃尔,伯格曼也有他的批评者。但瑕不掩瑜,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数百万人深深的共鸣。事实上,最了解电影的人,也就是那些制作电影的人–导演、编剧、演员、摄影师、剪辑师–都可能是以最大的敬畏之心来看待伯格曼的作品。
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我如此狂热得赞美他,在他去世的时候,很多报纸杂志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发表评论或接受采访。似乎除了再一次简单得称颂他的伟大之外,我并不能为这个可怕新闻添加任何价值。他们问道,伯格曼是如何影响我的。我说,他不可能影响到我,他是天才,而我不是;天才是学不来的,而他的魔法也无法传承。
当伯格曼作为一个伟大的电影人出现在纽约艺术馆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位年轻的喜剧作家和夜总会单口相声演员。一个人的作品真会受到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和伯格曼的影响吗?但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东西,那和天赋无关,甚至也无关乎才华,而是真正可以学习和发展的东西。我所说的通常宽泛得被称为职业道德,但实际上是最为基本的纪律性。
我学会了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努力交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作品,不让步于这个成王败寇的愚蠢世界,也不屈服于一味地扮演电影导演这个光鲜角色,而是专心制作电影,完成之后继续下一部。伯格曼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60部电影,迄今为止我只有拍摄了38部。也许我无法在电影品质上与他比肩,但我至少可以在数量上努力向他看齐。
|本文刊于2007年8月12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前身)上。
|翻译:Yifei (@迷影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