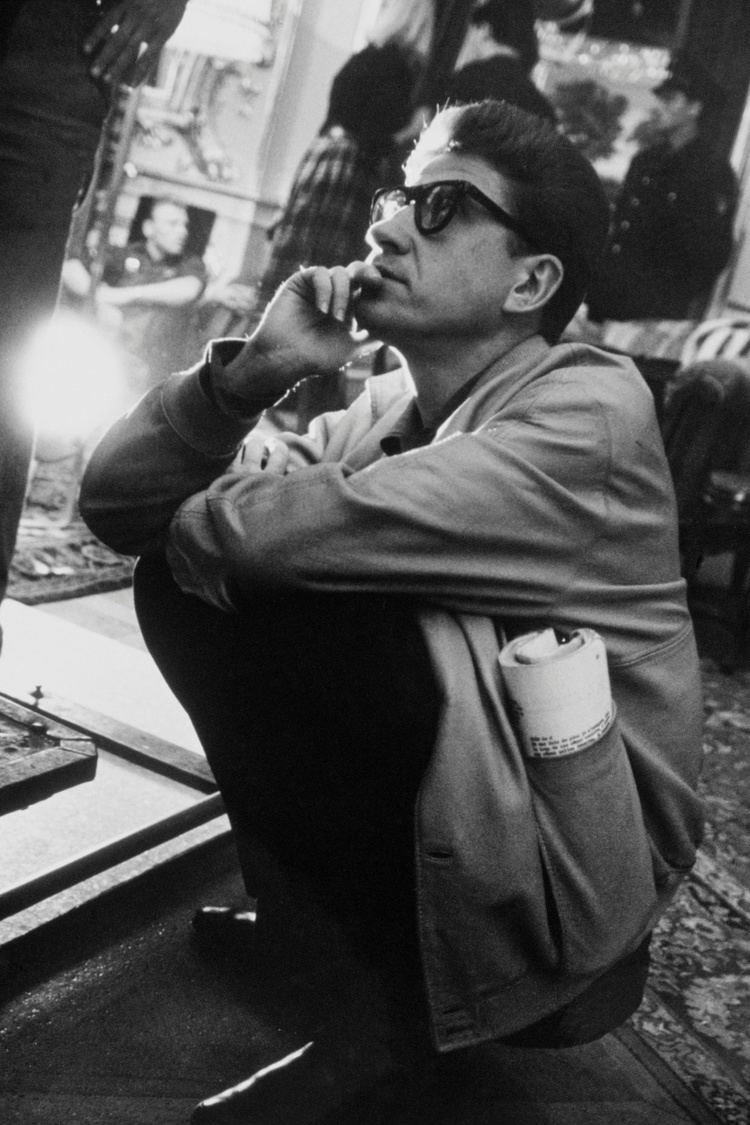
我们总不能阿Q地说:“每个人心中有一个雷乃”吧?阿伦·雷乃只有一个,只是基于人们对电影的“要求”不同,甚至说得更实在一点,对电影的“认识”不同,以致于这样的作者很可能在观众心中留下的“成分”也跟着不同。身为一个雷乃的“爱用者”,我想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谈一下雷乃不是什么,从“否定”否定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谈到一些基础问题。
不是装逼
当我们认真将雷乃当作一个“单位”来看,可以看到他19部剧情长片、一部电视纪录长片以及现存的八部短片(姑且不谈为别人主导的集锦影片如《远离越南》中的表现)有他自己发展的脉络,观众总不可能回避他的创作轨迹为他在不同时期带来的风貌。假使,他真有什么时候脱离了纯形式的挖掘,不正表示他也有拍“中规中矩”影片的时候吧?纵使从来没有真的规矩过,那也表示作为一个独立的、绝对的艺术家,他本来就有自己要表现的东西。
事实上,就算我们不考虑他从1970年代以后的偏向,光是考察他他所处的时代,亦不难发现他在创作上的一些语境条件。
首先我们观察到,1950年代的欧洲(特别就是在法国,因为他们投降得最快)普遍处在一种氛围,人们统称“表现主义”。这不难理解,19世纪中期也曾因为政府对人民的镇压,让当时的文人开发出后来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风格,其本质源于文人发现自己不该再处在“上帝视角”来看待他的人物、他所创造的世界。因为他们从人本身出发,以上帝视角看他自己虚构的世界,一如自封为上帝来检视苍生。但在发生了如此可怕的流血镇压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无能,自己在面对人、面对世界时的局限与无助。因此,如果说无法以一种极高视角来看待世事,那么至少可以回归到个人经验上,回到现实中。
1950年代的欧洲气氛也是类似,甚至,在近距离接触被纳粹洗礼过的欧洲,这种反省更强。别忘了,20世纪已经有各种传播工具,影像的传输迅速且有力。人们无法再回避,无法自欺欺人。艺术家面对他们手上的“材料”,他们究竟还能做什么?假如存在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先发现自身的局限,然后看到超越的可能性(以此来说,我们方知为何人们会将伯格曼的《第七封印》看做唯一一部真正存在主义精神的影片),艺术家面对他们的材料,无疑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
恰好存在主义首先也是从文学出发(然后才是哲学论调,许多跟存在主义相关的思维是从文学家笔下写出来的,毫不让人意外),文学家们首先发难也是合情合理。这才有了所谓的“新小说”的出现:20世纪初意识流丢掉了故事,现在来到新小说,甚至丢掉了主人公。抖开这最后的包袱,对创作者来说可能是有利的。雷蒙·柯诺在这个时期创造了以99种文体改写一简单小故事(如果还能称得上是“故事”的话)的《风格练习》,可说是相当符合“时代精神”;不久之后他甚至创造了另一个也纯属于文学的实验,《一百万首诗》──每一页的诗句可以单独被切割成活页,供读者自行搭配不同页的不同行诗句,而构成数十、上百万种组合情况。这是文学家对文学进行的材料实验。
雷乃等人(包括路易·马勒)和柯诺这样的怪杰也算是过从甚密的,雷乃日后将《苯乙烯之歌》交给柯诺负责对白撰写,当然也不令人意外。

雷乃曾表示过,他能有机会拍摄《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 1959)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益于新浪潮。在那个时代,“新浪潮”这个名词还是非常明确指向塞纳河右岸派诸将,包括来自《电影手册》的几位名家,以及像马勒、瓦汀这类明显向商业靠拢的新生代导演。《电影手册》诸君也好,马勒也好,这些人起码都有一定的创作自觉,马勒以其高等电影学院身分自豪,在浓厚的文化底蕴下,他自然也接触了与雷乃接近的训练背景。他曾在访谈中明白表示,当初就是想将他第二部剧情长片《恋人们》拍成属于他自己的《风格练习》;而他第三部长片直接拿柯诺的《地铁里的莎姬》来改编,更是无可指谪。
《手册》派的“年轻土耳其人”长期在电影资料馆里头“学习”,又在巴赞等文艺前辈的指导,加上有个写作平台粹炼思维,还有手提录音机的日益轻便对于访问他们心仪导演有所帮助,种种训练培养了他们的影像史观。有了这些包袱,便不难理解他们会积极于开发新的电影语言来与浩瀚的电影史进行抗衡;而熟悉电影史发展与各时期电影的发展情况,也让他们对于各种手法了然于心。待这批以写影评来当作电影实践的愤青,真正碰到摄影机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落实各种独特风格,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那么,这是新浪潮的创作背景。而雷乃自觉受益于新浪潮,在他有机会拍片时,岂能违背“潮流”?甚至我们还可以说雷乃也许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人,以致于他的“新浪潮时期”持续到1960年代末,几乎比真正的新浪潮运动持久了5年有余;就算不说保守,那也可能是他(其实还包括左岸派其他代表人物)执着于材料开发的探索,是基于他个人的坚持。
简单来说,雷乃前五部剧情长片包裹了“实验电影”的内核,有可能是“逼不得以”,他在一些访谈中虽然是轻描淡写地带到过,但也实实在在地表达过:“你能拍到的不见得是你会想拍的片”,言下之意心照不宣。
所以如果要批评雷乃所做的形式实验属于“装逼”,那么基本上这不是仅仅否定了整个新浪潮时期法国电影界的努力,甚至也拒绝了整个1950、60年代的时代精神。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雷乃自谦“没有创新”并非故弄玄虚。他的一切手法都是有迹可寻。他的情况就像拍摄《公民凯恩》时的奥逊·威尔斯,在他自认一切手法都有其渊源的同时,一定无法理解为何接受度这么低,甚至遭到诋毁。

不是不会讲故事
前述问题连带衍生的“否定”是雷乃不会讲故事。然而雷乃早就知道自己注定要花点时间,绕道通向形式的摸索上,因此他一开始就选定了可以发挥的题材,以致于这些片多少有一个共同点:稀释的戏剧性。比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故事”本身几乎毫无悬念:男子对女子的劝说,不论究竟解读的机制为何,这一个明显主轴是没有疑异的;甚至编导担心观众过多地被影片的实验给迷惑了,还透过各种方式(主要是路人甲乙的只字片语)来提醒观众“故事”是什么。有一说是雷乃希望拍一部观众不管什么时候进场或什么时候离场都没有损失的影片,当然,“损失”一说主要是指对于故事本身的接收,而不仅是对于影片本身的吸收;特别是,作品被拍得如此繁复,迫使观众反复重看是寻常情况!如此说来,真有“不会讲故事”之说吗?除非提出抗议的观众只能接受直线叙事。又如《广岛之恋》,有哪一位观众看不懂讲的是一对彼此都有家庭的异国男女却搞外遇的“故事”吗?又有观众不懂《莫里埃尔》中围绕伊莲娜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吗?《战争终了》的迪亚哥在面对国家政权变动而波及到情报工作者如他的情况下,对于身分、乔装的生活产生了各种质问与情感波动,难道又有怎么样的诲涩吗?
是角色牵引了形式的设置,这是雷乃自己明白表示过的:瞻前顾后的迪亚哥引动了所谓“闪前”的处理,而非雷乃要求编剧家去设想闪前的形式。史塔汶斯基则是一个不顾及即将降临身上的事情而仅担心死亡的人物,影片中尽是充满死亡的气氛,以凸显作为主人公的他所表现出来的心不在焉,甚至是走神、回避影片的“流动”。伊莲娜在生活上、精神上的混乱,也造成了《莫里埃尔》采取了破碎的组织结构。《夜与雾》也好,《广岛之恋》亦然,它们都无关乎“闪回”,而是透过人物来召唤过去的影像,所以时序上的交错主要是服务于观众,同时贴近剧中人物的状态。为了证明此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则干脆取消任何时序上的推论──特别是因为角色本身也没有定论!
(未完待续)
(编辑:李阳,徐明晨)
